國語·晉語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國語·晉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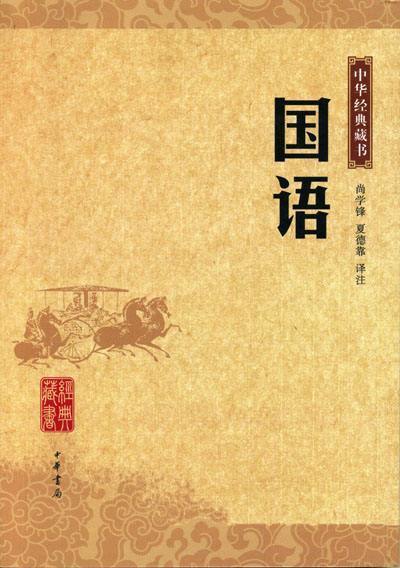 |
|
作品名稱;國語·晉語 創作年代;春秋末 作品體裁;文言散文 作者;左丘明 作品題材;歷史、傳說、政治 |
記錄了周朝王室和魯國、齊國、晉國、鄭國、楚國、吳國、越國等諸侯國的歷史。
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約前947年),下至智伯被滅(前453年)。包括各國貴族間朝聘、宴饗、諷諫、辯說、應對之辭以及部分歷史事件與傳說。
《晉語》系《國語》中一個篇目。《國語》的編撰,是以國分類,以語為主,故名《國語》。《國語》記錄了各國貴族間朝聘、宴饗、諷諫、辯說、應對之辭以及部分歷史事件與傳說,相傳為春秋末魯國左丘明所撰。[1]
原文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斗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餚。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餚。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餚。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
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雲不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
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鑒。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祗罹咎也。』雖驪之亂,其罹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不克饗,為人而已。」
士蒍曰:「誡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誡之,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
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強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之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複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噁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噁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國學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
蒸於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猛足乃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床笫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蒍,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拒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蒍以告,公悅,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否莫不信。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
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蒍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蒍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
士蒍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以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歿,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利眾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悅,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
驪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狄,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以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里克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曰:『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
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衣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乎!」狐突嘆曰:「以厖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雖勉之,狄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於稷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果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也。」
譯文
晉公子重耳流亡到北狄已經十二年。狐偃說:「當初我們到這兒來,不是因為狄地安樂,而是因為這裡可以成就大事。我曾說過:『狄地離晉國近出走時容易到達,窘迫中可以得到些資助,通過休整可以選擇更有利的環境,因此才居留下來。』現在已經居住很久了,住久了一切便會停頓下來,那種苟且怠惰的心理也會隨着產生,誰還能振作有為?為什麼不趕快走呢!當初我們不到齊、楚兩國去,是怕路途太遠。如今養精蓄銳了十二年,可以遠行了。齊桓公年紀大了,但是他氏想親近晉國的。管仲去世後,桓公身邊儘是些讒諂小人,謀劃沒有人來匡正。一切政事推行到半途就想到當初有管仲的忠告多好。他一定經常追想管仲生前說過的話來加以採用,希望求得一個好結果。齊國與鄰國既已相安無事,就會謀求和遠方的諸侯搞好關係,我們遠方的人去投奔,就不會有什麼過錯。現在正值桓公的暮年,正是可以親近他的好時機。」大家都覺得狐偃說得很對。
於是重耳一行便出發了。他們路過衛國的五鹿時,向田野里的農夫討飯吃,農夫卻把地里的土塊給他們,重耳很生氣,想要鞭打他。狐偃說:「這是上天的賞賜啊。民眾獻土表示順服,對此我們還別有什麼可求的呢?上天要成事必定先有某種徵兆,再過十二年,我們一定會獲得這片土地。你們諸位記住,當歲星運行到壽星和鶉尾時,這片土地將歸屬我國。天象已經這樣預示了,歲星再次行經壽星時,我們一定能獲得諸侯的擁戴,天道十二年一轉,應該從現在算起。占有這塊土地時,應當是在戊申這一天吧!因為戊屬土,申是說擴大土地的意思。」於是重耳再拜叩頭,把泥土收下裝在車上。然後,他們一行人便往齊國去了。
齊桓公把宗室的女兒嫁給重耳為妻,待重耳很好。贈送給他二十輛馬車八十匹馬,重耳心滿意足的表示打算老死在齊國了。他說:「人生就是為了安樂,誰還去管別的什麼呢?」
齊桓公死後,孝公即位。這時,諸侯都不在聽齊國指揮。狐偃知道齊國不可能幫助重耳返國,也曉得重耳已安於留在齊國,並準備老死在此的想法,想要離開齊國,又擔心重耳不肯走,於是就和隨從重耳一起逃亡的人在桑林中商量這件事。有一個女奴正好在樹上採桑葉,但誰也沒有發覺她。採桑女奴報告重耳的妻子姜氏,姜氏怕泄露消息,便把她殺了,然後對公子重耳說:「你的隨從想要同你一起離開齊國,那個偷聽到這事的人我已經殺掉了。你一定要聽他們的,不能猶豫不決,遇事猶豫不決,就不能成就天命。《詩經》上說:『上帝暗中保佑着你,你心裡千萬不能懷有二心。』武王知道天命,因此能成大事,猶豫不決怎麼能做到呢?你因晉國有危難而來到這裡。自從你離開以後,晉國沒有一年安寧過,百姓也沒有一個穩定的國君。上天還沒有要晉國滅亡,現在能拯救晉國的除了您沒有其他人了。將來能擁有晉國的,不是您還有誰?希望您好好努力!上天在保佑你,遲疑不決一定會惹禍遭殃。」
公子重耳說:「我是不會被人說動的了,一定要老死在這裡。」姜氏說:「這樣不對。《周詩》上說:『那些風塵僕僕的行人,時常惦念着自己要辦的事,唯恐來不及把事情辦好。』晝夜奔忙在道路上的人,連一會兒安坐休息的工夫也沒有,這樣尚且還怕來不及把事情做好。更何況那些隨意放縱嗜欲、貪戀安逸的人,怎麼可能有什麼成就呢?一個人不追求及時完成大業,又怎麼能達到目的呢?日月如梭,時光不停,一個人哪能只想獲得安逸呢?西方的書上有句話說:『貪圖享樂和安逸,是要敗壞大事的。』《鄭詩》上說:『仲子雖可懷念,但人們說三道四也很可怕啊。』以前管仲說的話,我也曾聽到過。他說:『如果一個人像害怕疾病一樣地敬畏天威,是人中的最上者。只知道眷戀私慾隨大流,是人中的最下者。看到可眷戀的事物,就想起天威的可畏,是中等人。只有敬畏天威如害怕疾病一樣,才能樹立權威,統治人民。有聲威才能居於民上,對天威無所畏懼,則將受到懲罰。只知貪戀私慾隨大流,那離建立聲威就很遠了,因此說是人中的最下者。照以上引喻的話來看,我是願做中等人的。《鄭詩》上所說的話,我是願意遵從的。』這就是大夫管仲所以能夠治理齊國,輔佐先君成就霸業的原因。現在你要丟棄它,不是太難於成大事了嗎?齊國的政治已經衰敗了,晉君的無道已經很久了,跟隨您出亡的人所謀慮的事時忠於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公子得晉國的日子快到了。你去當晉國的國君,可以解救百姓,如果放棄這事業,那簡直不算人了。齊國的政治敗壞不宜久居,有利的時機不可錯過,你的追隨者的一片忠誠不可丟棄,眼前的安逸不可貪戀,你一定要趕快離開齊國。我聽說,晉國最初受封的時候,那年歲星正在大火星的位置,也就是閼伯的星辰,實際上記錄着商朝的命運。商代享有天下,一共傳了三十一位國君。樂師和史官的記載說:『唐叔的後裔享有晉國,將同商代國君的數目一樣。』現在還不到三十一位的半數。晉國紛亂的局面不會長久下去,公子中只有您在百姓中享有聲威,您肯定能成為晉國國君的。為什麼還要貪戀眼前的安逸呢?」但是,公子重耳仍然聽不進去。
姜氏與子犯商量出一條計策,把公子重耳灌醉了,載在車上離開齊國。重耳酒醒後,拿起一把戈就追打子犯,說:「假如事業不成功,我就是吃了你舅舅的肉,也不能滿足啊!」子犯一邊逃一邊回答說:「假如事業不成功,我還不知道死在哪裡,誰又能與豺狼爭着吃野地里得死屍呢?假如將來事業成功的話,那麼公子不也就有了晉國最柔脆嘉美的食品,都是你愛吃的。我狐偃的肉腥臊難聞,您哪裡會吃得進口呢?」於是,一行人就離開齊國,啟程上路了。
重耳一行人經過衛國,當時衛文公因憂慮邢人、狄人聯合入侵,便沒有以禮相接待。寧莊子對衛文公說:「按禮儀接待賓客,是國家的綱紀,親近該親近得人,是人民團結的紐帶,對有德行的人態度親善,是立德的基礎。國家沒有綱紀不可能長存,人民不團結就不可能堅固,不善也不可能立德。這三者,是國君應當謹慎對待的。如今您輕易拋棄它,恐怕不應該吧!晉公子重耳是個賢人,又是衛國該親近的人,您不以禮相待,就是拋棄了以上所說的三種美德。臣因此說要請君王認真地考慮考慮。衛國的祖先康叔,是周文王的兒子。晉國的祖先唐叔,是周武王的兒子。為周朝統一天下建立大功的是周武王,上天將降幅於周武王的後代子孫。只要姬姓仍繼續擁有周王室的天下,那麼守着上天所聚集的財富和民眾的,一定是周武王的後代。周武王的後代中,只有晉國繁衍昌盛,晉國的後代中,公子重耳最有德行。現在晉國在位的君主都無君德,上天保佑有德的人,晉國能守住宗廟祭祀的人,一定是公子重耳了。如果重耳能夠返國復位,修其德行,安撫百姓,必然獲得諸侯的擁護,討伐以前對他無禮的國家。君王如果不早作打算,那衛國就不免要遭到討伐了。小人因此感到害怕出現這種後果,不敢不盡心把話說在前頭。」但是,衛文公聽不進寧莊子的話。
重耳一行自衛國經過曹國,曹共公也不以禮相待,並且聽說重耳的肋骨生得連成一片,因此就很想看看是什麼樣子,故意將重耳等安排在旅舍里,打聽到重耳將要洗澡,安排自己隱藏在暗處突然走近他身邊去偷看他的肋骨。
曹國大夫僖負羈的妻子對她丈夫說:「我看晉公子是個賢人,他的隨從都是國相的人才,這其中只要有一個人輔佐他,他將來必定能回到晉國即位。他一旦為晉國國君,就會討伐對他無禮的國家,那麼曹國就是他首先開刀的了。你為什麼不早一點表示自己的不同態度呢?」僖負羈便饋贈了一盤食品給重耳,盤底還放着一塊璧。重耳接受了食品,退回了璧。
僖負羈對曹共公說:「晉國公子現在經過此地,和君王的地位相當,難道不應當以禮相待嗎?」曹共公回答說:「諸侯各國在外逃亡的公子多了,誰不經過此地呢?逃亡的人都沒有什麼禮節可言,我怎麼能一一都以禮相待呢?」僖負羈回答說:「我聽說,愛護親屬,尊重賢人,是政事的主幹。以禮待客,同情窮困,是禮儀的根本。用禮來治理國政,是國家的常道。失去了常道,就不能自立,這是君主所了解的道理。對國君來說沒有私親,只是以國為親。曹國的祖先叔振,是周文王的兒子,晉國的祖先唐叔,是周武王的兒子,周文王、武王的功勞,在於建立了許多姬姓的封國。所以二王的後代,世代都不拋棄相親相愛的關係。如今國君丟棄了這一傳統,是不愛親屬。晉公子重耳十七歲流亡國外,三個具有卿相之才的人追隨他,公子重耳可稱得上是賢人了,而君王輕視他,是不尊重賢人。凡是知道晉公子出逃流亡這件事的,不能不說他值得同情。他的資格等同於國賓,不可不以禮相待。如果失去了這兩者,那就是不以禮待客,不同情處於困境中的人傑。守着上天所賜給的爵邑和財富,應當施行於符合道義的事。有符合道義的事而不願去做,那麼積累再多財富一定會缺失。玉帛和酒食,如同糞土一般,愛重糞土而毀棄三種立國的常道,那就會失去君位,丟掉聚集起來的財富,國事出了問題還不自感危難,但恐怕不可以吧?希望國君好好想一想。」曹共公不聽從僖負羈的勸告。
公子重耳經過宋國,因重耳與宋國司馬公孫固關係很好。公孫固便對宋襄公說:「晉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十幾年,已經由孩子長大成人了,喜歡做好事而不自滿,像對待父親一樣事奉狐偃,像對待老師一樣事奉趙衰,像對待兄長一樣事奉賈佗。狐偃是他的舅舅,仁慈而又足智多謀。趙衰是為晉獻公駕御戰車的趙夙的弟弟,富於文才而為人忠貞。賈佗是晉國的公族,見多識廣而謙恭有禮。這三個人實在對公子重耳影響很大的。公子平時對他們謙下恭敬,每逢有事都要諮詢他們的意見,從年幼到長大成人始終如此,不稍懈怠,對他們總是禮貌有加。對人有禮,一定會得到忠心的報答。《商頌》上說:『商湯急於尊賢下士,國內尊重人才的風氣一天天向上升高。』尊賢下士,就是有禮的表現。請君王好好地考慮考慮。」宋襄公聽從了他的意見,贈送給重耳二十輛馬車八十匹馬。
公子重耳經過鄭國,鄭文公也不加禮遇。鄭國大夫叔詹勸諫鄭文公說:「臣聽說,親近上天要護助的人,秉承先君的教誨,對兄弟之邦以禮相待,資助窮困的俊傑,上天是會保佑他的。如今晉公子有三種天意的吉兆,該是上天要護助他吧。自古以來同姓的男女不結婚,怕的是子孫不會昌盛。狐氏與晉一樣都是唐叔的後代。重耳的母親狐姬是伯行的女兒,生了重耳。重耳長大成人並且才能出眾,雖然逃難離國,但舉動得體,長久處於窮困而沒有什麼毛病,這是第一件得天保佑的。同生的九個兄弟中,現在只有重耳還活着,雖然遭到陷害而流亡在外,而晉國國內卻一直不安定,這是第二件得天保佑的。現在晉國百姓對晉侯怨聲載道,日甚一日,國內外都拋棄了他;重耳則天天注重提高品德,有狐偃、趙衰等為他出謀劃策,這是第三件得天保佑的。《周頌》上說:『天生萬物在岐山,太王大大地發展了它。』荒,就是大發展的意思。能夠大發展上天所生成的,可以稱得上是親近上天了。晉、鄭兩國是兄弟之國,我國的先王鄭武公和晉文侯曾同心協力,捍衛周王室,輔佐周平王,平王親自勉勵褒獎他們,並且賜給他們作為憑信地盟書,說:『世世代代互相扶持。』如果說要親近上天要護助地人,那親近公子重耳這樣獲得三種吉兆的人,可以稱得上是得天助了。如果說遵循先王的遺訓,晉文侯和鄭武公輔助周王室的業績,可稱得上是有先人遺訓。如果說對兄弟要以禮相待,晉、鄭兩國同姓相親,又有周平王的遺命,可稱得上是兄弟。如果說要資助貧困中的俊傑,公子從小到大流亡在外,乘車周曆各諸侯國,可稱得上窮困中的俊傑。拋棄了這四種美德,會招致天禍,恐怕不行吧!請君王好好地想一想。」鄭文公沒有聽從這番勸告。
叔詹又說:「君王如果不能以禮相待,那麼就請殺了他。有一句諺語說:『高粱小米不讓它生長,就不能開花結果。高粱的種子長不出高粱,是因為不讓他生長得茂盛。小米的種子長不出小米,是因為不讓它繁育。種什麼得什麼,這是沒有疑問的,這才是因地制宜培養德行的根本。』」鄭文公還是不聽。
重耳一行到楚國去,楚成王用周王室待諸侯的禮節款待他,宴會上獻酒九次,院子裡陳列的酒肴禮器數以百計。公子重耳想要推辭,子犯說:「這是上天的意志,您還是接受吧。一個逃亡在外的人,竟受到國君之禮的接待,不是同等身份地位,卻像對待國君那樣陳設禮物,若不是上天有靈,誰會使楚成王有這樣的想法呢?」
宴會之後,楚成王問公子重耳說:「您如果能夠回到晉國當國君,用什麼來報答我呢?」公子重耳跪拜叩頭說:「美女、寶石和絲帛,您有的是。鳥羽、旄牛尾、象牙和犀皮革,貴國的土地上都生產。那些流傳到晉國的,已經是君王剩下來的,又叫我用什麼來報答您呢?」楚成王說:「雖然這樣,我還是想聽聽您怎樣報答我。」重耳回答說:「要是托您的福,我能夠回到晉國,將來萬一晉、楚兩國交戰,在中原相遇,我願避開君王后退九十里。要是這樣還得不到您的諒解,那麼我只好左手拿着鞭子和弓,右邊掛上弓囊箭袋,奉陪您君王較量一番。」令尹子玉說:「請殺掉晉公子重耳。不殺的話,一旦他回到晉國,必然會對楚軍造成憂患。」楚成王說:「不行。即使將來楚國軍隊受到威脅,那是我們自己不修德的緣故。我們自己不修德,殺了他又有什麼用?如果上天保佑楚國的話,誰又能對楚國造成威脅呢?如果上天不能保佑楚國,那麼晉國廣大的土地上,難道就不會出現其他賢明的國君嗎?而且晉公子為人通達又富於文辭,處在窮困之中,卻不肯逢迎諂諛,又有三位卿相之材侍奉他,這是上天在保佑他啊。天意要叫他復興,誰能夠毀掉他呢?」子玉說:「那麼就請把狐偃扣留起來。」楚成王說:「不行。《曹詩》上說:『那個沒落貴族的兒子,中途拋棄了他的家室。』這是犯了一個錯誤。如果明知是錯的再去仿效,那就錯上加錯了。仿效錯的, 這不符合禮啊。」
這時正巧晉懷公從秦國逃回了晉國。秦穆公惱恨晉惠公、晉懷公父子,就派人到楚國來召請公子重耳,楚成王便用厚禮把重耳送到了秦國。
秦穆公把五個宗族的女子嫁給重耳,自己的女兒懷嬴也是其中之一。有一次,公子重耳叫懷嬴捧着倒水的器具給他澆水洗手,洗完了,便揮手叫她走開。懷嬴生氣說:「秦、晉兩國是同等的國家,你為什麼如此輕視我?」重耳害怕秦穆公知道後生氣,便解去衣冠,將自己囚禁起來,聽候處理。秦穆公會見重耳時,說:「我和嫡夫人生的女兒中,懷嬴是其中最有才能的。以前公子圉在秦國作人質時,她任宮中的女官。現在想叫她和公子成婚,恐怕因為她曾是公子圉的妻子,從而遭受不好的名聲。除此之外,那就沒有其他什麼不妥了。我不敢用正式的婚禮把她歸於你,是因為喜歡她的緣故。這次使公子解衣受辱,是寡人的罪過。如何處置她,完全聽憑公子的意見。」
重耳想推辭不娶懷嬴,胥臣說:「同姓同德的才是兄弟。黃帝的兒子有二十五人,其中同姓同德的只有二個人罷了,只有青陽與夷鼓都姓己。青陽是方雷氏的外甥,夷鼓是彤魚氏的外甥。其他同父所生而異姓的,四個母親的兒子分別為十二個姓氏。凡是黃帝的兒子,有二十五宗。其中得姓的有十四人,分為十二姓,那就是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和依。只有青陽與蒼林氏的道德及得上黃帝,因此都姓姬。德行相同竟這樣難。以前少典娶了有氏,生了黃帝和炎帝。黃帝依姬水而成長,炎帝依姜水而成長,長大以後兩人的德行不同,因此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兩帝動用武力互相殘殺,就是因為德行不同的緣故。姓不同德行就不同,德行不同就不同類。不同類雖然關係接近,男女可以嫁娶成婚,為的是生育兒女。姓相同德行就相同,德行相同心就相同,心相同志向就相同。志向相同雖然關係遠,男女不可嫁娶成婚,是怕褻瀆了恭敬之情。褻瀆就會產生怨恨,怨恨就會產生災禍,災禍產生就會消滅同姓。因此娶妻要避開同姓,是害怕禍亂災難。因此德行不同可以合姓成婚,德行相同可以以義結合。以義結合可以生利,利又可以使同姓相厚。姓和利相互聯續,相成而不離散,就能保持穩固,守住土地和住房。現在你和子圉的關係,如同道路上的陌生人那樣,取他所拋棄的人,以成就返國的大事,不是也可以嗎?」
公子重耳對子犯說:「你看如何?」子犯回答說:「你將要奪取他的國家,娶他的妻子又有什麼不可以呢,只管聽從秦的命令吧。」重耳又問趙衰:「你看如何?」趙衰回答說:「禮書上說:『將要向別人請求,一定要先接受別人的請求。想要別人愛自己,一定要先愛別人。想要別人聽從自己,一定要先聽從別人。對別人沒有恩德,卻想有求於人,這是罪過。』現在你最好跟秦國聯姻以服從他們,接受他們的好意以與他們相親愛,聽從他們以使他們對你施恩德。只怕不能這樣,又有什麼可懷疑的呢?」於是重耳就向秦國納聘禮,締結婚約,並且親自迎懷嬴成親。
有一天,秦穆公將設宴款待公子重耳,重耳叫子犯隨從。子犯說:「我不如趙衰那樣善於辭令,請讓趙衰跟您同去吧。」於是,重耳便叫趙衰隨從前往。
秦穆公用款待國君的禮節來招待重耳,趙衰做賓相,完全按照賓禮進行。宴會結束後,秦穆公對大夫們說:「舉行禮儀而不能夠善始善終,是恥辱。內在的思想感情和外面的禮貌不一致,是恥辱。形式華麗而沒有實際內容,是恥辱。不估量自己的能力而施恩德,是恥辱。施德於人而不能助人成功,是恥辱。不關閉這五種羞恥之門,沒有資格做為諸侯。不關閉這五恥之門,對外用兵就會一無所成。你們在這方面必須恭敬謹慎從事啊!」
在第二天舉行的宴會上,秦穆公朗誦了《采菽》這首詩,趙衰讓重耳下堂拜謝。秦穆公也下堂辭謝。趙衰說:「國君用天子接待諸侯的待遇來接待重耳,重耳怎敢有苟安的想法,又怎敢不下堂拜謝呢?」拜謝完畢後又登堂,趙衰讓公子朗誦《黍苗》這首詩。趙衰說:「重耳仰望國君,就像久旱的黍苗仰望上天下雨一樣。如果承蒙國君庇護滋潤,使他能成長為顆粒飽滿的穀子,奉獻給晉國的宗廟,那是依靠國君的力量啊。國君如果能發揚光大先君秦襄公的榮耀,東渡黃河,整頓軍隊使周王室再度強大起來,這是重耳的願望啊。重耳如果能得到國君的這些恩惠而回到晉國主持宗廟祭祀,成為晉國百姓的君主,得到封國,是會聽從您的安排的。國君如果能放心大膽地任用重耳,四方的諸侯,誰還敢不小心翼翼地聽從您的命令呢?」秦穆公嘆息道:「這個人將會獲得他想得到的,哪裡是單單靠我一個人的幫助呢!」秦穆公朗誦了《鳩飛》這首詩,重耳也朗誦了《沔水》這首詩。秦穆公又朗誦《六月》這首詩,趙衰讓公子重耳下堂拜謝。秦穆公也下堂辭謝。趙衰說:「國君把輔助周天子、匡正諸侯國的使命交付給重耳,重耳怎敢有怠惰之心,怎敢不遵從您的意願呢?」
公子重耳親自占卜問卦,起卦說:「上吉卦,將得到晉國。」內卦得震下坎上的《屯》卦,外卦得坤下震上的《豫》卦,其中兩個陰乂的數字都是八,全陰。筮史占此兩卦後都說:「不吉利。閉塞不通,根據爻象將無所作為。」胥臣(司空季子)推斷說:「吉利。這在《周易》上,二卦都稱『利於建立侯國』。得不到晉國來輔助周王室,怎麼能立為諸侯?我們起卦說『上有晉國』,卦辭告訴我們說『利於建立侯國』,是得到國家的意思,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吉利的呢!《震》卦,象徵隆隆如雷的車聲。《坎》卦,象徵水。《坤》卦,象徵土地。《屯》卦,象徵富厚。《豫》卦,象徵喜樂。《震》為車,內卦外卦都有車聲,《坤》卦表示順利的意思;卦內還有《艮》象、《坎》象,水在山上為泉是源源不斷的財富,土地富厚而百姓在它的養餘下安樂。如果不能得到晉國,怎麼能應合這些卦象呢?《震》卦,代表雷震和車聲。《坎》卦,有勞、水和眾多的意思。它們主持雷震和車聲,還崇尚水和眾。車聲隆隆如雷震,是威武的象徵。眾人歸順,是文德的象徵。文武都具備,這是最富厚的了。所以稱為《屯》卦。它的卦辭說:『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震》卦主雷震,是成長的意思,所以說是『元』。眾人歸順,是服善,所以說是『亨』。內卦有雷震,所以說是『利貞』。《震》卦在上是有威,《坎》卦在下是順從,象徵着必定能稱霸。只是在小人之事上不成功,是因為堵塞不通,所以說『不利於出門』,那是指一個人的行動。民眾歸順而且有武威,所以說『利於封侯建國』。《坤》卦,指母親。《震》卦,指長男。母親年老,兒子強健,所以說《豫》卦安樂。它的卦辭說:『有利於封侯建國,出兵打仗。』就是指平時安樂,出兵威武的意思。這兩卦,都是得國的吉卦啊。」
晉惠公十四年十月,晉惠公病死。十二月,秦穆公派軍隊把公子重耳送回晉國。到了黃河邊上,子犯把祭祀用的璧玉交給重耳,說:「我跟隨您乘車周轉,在天下巡行,臣的罪過已經太多了。我自己都知道得罪了您,何況您呢?我不忍心因此而死,請公子就此允許臣離開吧。」重耳說:「假如我不跟舅舅同心同德,我願以黃河水賭咒為誓!」說着就把那塊璧扔進了黃河裡,來表明自己的誠信。
晉國史官董因在黃河邊上迎接重耳,重耳問道:「我這次回來能成功嗎?」董因回答說:「現在太歲星出現在大梁區域,這象徵您將要成就大事。您即位的第一年,是在實沈星的位置。實沈的故城,正是晉人居住的地方。晉國因此才興盛起來的。如今正好應合在您身上,沒有不成功的。您出逃的時候,歲星在大火星的位置。大火星,就是閼伯星,也稱為大辰星。辰星代表農事吉祥,周的祖先后稷據此以成就農事,晉的始祖唐叔也是歲星在辰的那年受封的。瞽史的記載說:子孫後代繼承先祖,如同穀物蕃育滋長。因此必定能得到晉國。我占筮,得到《泰》卦陰爻的數字是八。說:這是指天地亨通,小的去大的來。現在到時候了,怎麼會不成功呢?而且您是歲星在辰時出走的,又於歲星在參時回國,這些都是晉國吉祥的徵兆,是上天大的歷數。成功穩握在手,必定能稱霸諸侯。子孫後代都仰賴它,您不必害怕。」
重耳渡過了黃河,召集令狐、臼衰、桑泉三個地方的長官,他們都投降了。晉國人感到害怕,晉懷公逃亡到了高梁。呂甥、冀芮率領着晉軍抵抗,甲午那天,晉軍駐紮在廬柳。秦穆公派秦國大夫公子縶到晉軍中去勸說他們不要抵抗,結果晉軍退走,駐紮在郇城。辛丑日,狐偃與秦、晉兩國的大夫在郇城會盟訂約。壬寅那天,重耳接管了晉國軍隊。甲辰日,秦穆公返回秦國。丙午日,重耳進入曲沃。丁未日,進入首都絳城,在晉武公廟即位為君。戊申日,晉文公派人在高梁刺殺了晉懷公。
起先,晉獻公派寺人勃鞮到蒲城去行刺公子重耳,重耳跳牆逃走,被勃鞮砍斷了他的衣袖。到重耳返國即位,勃鞮來求見,晉文公拒絕接見他,說:「以前驪姬進讒言陷害我的時候,你在屏門內向我射箭,還到蒲城圍困我,砍斷了我的衣袖。又為晉惠公追蹤我到渭水岸邊來謀殺我,惠公命令你三天到達,可是你隔一夜就來了。你違反獻公、惠公的命令,竭盡心力想要殺我。我屢次遭到你的逼迫,我和你又有什麼舊怨呢?你回去好好想想,改日再來見我。」勃鞮回答說:「我以為您已經懂得君臣之道,因此才返回晉國,原來您到現在還不懂得,可能您又將失去國家出走了。事奉君主忠心不二,才是人臣;不因私人好惡而改變原則,才是做君主的道理。君要像君,臣要像臣,這是歷來聖明的教誨。能始終守住這一教誨,才可成為統治百姓的君主。在獻公、惠公的時候,你只是蒲人和狄人,跟我有什麼關係呢?剷除國君所痛恨的人,盡全力去完成,怎麼能說是懷有二心呢?如今君主即位以後,難道說就沒有蒲人、狄人了嗎?商代的伊尹流放了太甲,終於讓他成為賢明的君王。齊國的管仲射傷過齊桓公,最終使桓公稱霸於諸侯。在乾時戰役中,管仲用申孫之箭射中了桓公的衣帶鈎,衣帶鈎比衣袖口更接近要害,而桓公卻沒有怨言,任他為國相,一直到死,終於成就美名。如今您的德量氣度,為什麼不能寬大些呢?憎惡您應該喜愛的忠臣,您的君位還能保持長久嗎?您實在是不能恪守住前人的教誨,拋棄了做君主的道理。我只是一個有罪的閹人,又有什麼可擔心的呢?您不接見我的話,您可不要後悔啊!」
這時呂甥、冀芮害怕受到文公的迫害,後悔當初允許文公回國,策劃陰謀作亂,打算在己丑那天焚燒文公的宮殿,乘文公出來救火的時候加以殺害。勃鞮知道這一陰謀,因此來求見晉文公。文公馬上出來接見,說:「難道不是像你所說的那樣麼,但確實是因我怨恨在心,我請從此改過。」勃鞮就將呂甥、冀芮的陰謀告訴了文公。文公很害怕,乘着驛車走小道逃脫,脫身到王城秘密會見了秦穆公,告訴了穆公呂、冀作亂的陰謀。等到己丑那天,文公的宮殿果然起火,呂甥、冀芮兩人沒有捉到文公,於是跑到黃河邊上,秦穆公用計把他們誘騙來殺了。
晉文公出逃的時候,侍臣豎頭須是負責管理錢財的,沒有跟從流亡。文公回國後,他請求進見,文公推託說正在洗頭而拒絕接見。豎頭須對傳達的人說:「洗頭的時候必須低着頭,一低頭心就會倒過來,心倒過來所想的就會反過來,無怪我不能被接見了。跟從流亡的是牽馬韁繩效勞的僕人,留在國內的是國家的守衛,何必一定要認為留在國內的人有罪呢!身為國君而跟一個普通人為仇,那害怕的人就多了。」傳達的人把這番話轉告給文公,文公趕緊接見了他。
晉文公元年,春天,文公和夫人嬴氏從秦國的王城回到晉國。秦穆公派衛士三千人護送,都是得力幹練的衛士。
晉文公會見百官,授與官職,任用功臣。免除舊的債務,減免賦稅,布施恩惠,捨棄禁令,分財給缺乏勞力的人,救濟貧困,提拔有才德而長期沒升遷的人,資助沒有財產的人。減輕關稅,修治道路,便利通商,放寬對農民的勞役。鼓勵發展農業,提倡互相幫助,節省費用來使資財充足。利器便民,宣揚德教,以培養百姓的純樸德性。推舉賢良,任用有才能的人,制定官員規章,按法辦事,確立上下尊卑的名分,培育美德。表彰舊臣中有功勞的,親近同宗的親人,榮耀賢良,尊寵貴臣,獎賞有功勞的人,敬事老人,禮待賓客,親近舊日的友人。胥、籍、狐、箕、欒、郤、桓、先、羊舌、董、韓等十一族,都在朝廷擔任官職。姬姓中賢良的人,擔任朝廷內務官。異姓中有才能的人,擔任縣、鄉的地方官。王公享用貢賦,大夫收取采邑的租稅,士受祿田,一般平民自食其力,百工、官商之官從國庫領取糧食,皂、隸按其職務領取口糧,卿大夫的家臣食用取自大夫的家田。於是政治清明,民生豐安,財用充足。
晉文公元年的冬天,周襄王因為同母弟率狄人攻陷都城而出走避難,住到鄭國的汜地,派人到晉國告急,又派人到秦國求援。子犯說:「百姓親近君王,但還不知道君臣大義,您何不送周襄王回國,以此來教導百姓懂得道義呢?如果您不送,秦國就會送襄王回國,那就會失去事奉周天子的機會,還憑什麼來求得諸侯盟主的地位呢?如果不能修養品德,又不能尊奉周天子,別人怎麼會依附呢?繼承晉文侯的業績,建立晉武公的功德,開拓國土,安定疆界,就在於這次了,請您努力做好這件事。」文公聽了很高興,於是就送重禮給草中的戎人和驪土的狄人,向他們借兵與晉軍協同作戰打開東進的道路。
晉文公二年,春天,文公率領上軍、下軍順黃河東下,駐紮在陽樊。右翼部隊在溫地俘虜了昭叔,把他殺死在隰城。左翼部隊去鄭國迎接周襄王。襄王返回了成周,在郟城復位。周襄王特設甜酒款待,賜給文公命服、祭肉、幣帛。文公請求死後用掘地道的天子墓葬,襄王沒有允許,說:「這是天子所用的葬禮,國家不可以有兩個天子,否則周天子以後無法發布政令。」賜給文公南陽地區所屬的陽樊、溫、原、州、陘、、組、攢茅等八邑的田地。陽樊人不願歸服。文公派軍隊包圍了它,準備屠殺陽樊的百姓。陽樊守臣倉葛高呼說:「你幫助周襄王恢復王位,是為了遵循周禮呀。陽樊人由於不熟悉你的德行政令,而不接受你的命令。你就要屠殺他們,這不是又違反了周禮嗎?陽樊人有夏、商的後代和遺留下來的法典,有周王室的軍隊和民眾,有樊仲山甫一樣的守官,這些人即使不是樊氏的守臣,也都是王室的父兄甥舅。你安定周王室卻屠殺周的親族,百姓怎麼會依附呢?我私下斗膽向軍吏陳說此情,請您仔細地考慮考慮!」晉文公說:「這是君子所說的話啊。」於是就下令撤掉包圍,放陽樊的百姓出城。
晉文公出兵討伐原國,命令攜帶三天的口糧。到了三天,原國還不投降,文公就下令晉軍撤退。這時晉軍間諜出城來報告說:「原國最多再能支持一二天了!」軍吏將這一情況匯報給晉文公,文公說:「得到原國而失去信義,那又依靠什麼來治理百姓呢?信義是人民賴以生存的保障,因此不可失信。」於是晉軍便撤離了原國,到了附近的孟門地方,原國便宣布投降了。
晉文公即位第四年,楚成王出兵攻打宋國。文公率領齊、秦兩國的軍隊征伐曹、衛兩國,以解救宋都之圍。宋國派門尹班到晉國告急,晉文公對大夫們說:「宋國來告急,如果丟下宋國不管,那麼宋國就會與我國斷交。如果請求楚國退兵解圍,楚國也不會答應。我想攻打楚國,齊、秦兩國又不願意,你們看怎麼辦?」先軫說:「不如讓齊、秦兩國都去怨恨楚國。」文公說:「那行嗎?」先軫回答說:「讓宋國捨棄我國,而去向齊國和秦國送財物,通過齊、秦去請求楚國退兵。我國將獲得的曹、衛二國土地賜給宋國。楚國喜歡曹國和衛國,必定不答應齊國和秦國的請求。齊、秦兩國請求不成,必然因此而怨恨楚國,然後我國再叫齊、秦兩國參戰,兩國就不會不願意了。」晉文公聽了很高興,因此將曹、衛兩國的田地賜給了宋國。楚國的令尹子玉派宛春來傳話,說:「請你們恢復衛侯的君位,把土地退還曹國,我們也解除對宋國的包圍。」子犯發怒說:「子玉真無禮啊!晉君只得到一項好處,而子玉卻得到兩項好處,一定要攻打他。」先軫說:「你應該允許他的請求。我們不答應曹、衛兩國的請求,等於不允許解除對宋國的包圍,宋國投降了楚國,楚國的兵力不是更強大了嗎?這樣,楚國一句話對三個國家施了恩,而我們一句話卻招了三個國家的怨。怨恨已經多了,戰爭難以打下去。不如私下允許恢復曹、衛兩國,以離間他們,然後逮捕宛春來激怒楚國,等戰爭打起來之後再作打算。」晉文公很高興,於是把宛春囚禁在衛國不放。
楚令尹子玉果然被激怒,他下令解除了對宋國的包圍,轉而追逐晉軍。楚軍擺開戰陣之後,晉文公下令退卻三十里,晉國的將士請戰說:「作為國君卻避開敵國的臣子,是一種恥辱。而且楚軍已經疲勞,必然戰敗,我軍為什麼要撤退呢?」子犯說:「你們都忘記了以前晉文公在流亡楚國時所作的諾言了嗎?我狐偃聽說過,用兵作戰,理直才會氣壯,理曲士氣就會低落。我們尚未報答以前楚國對晉文公的恩惠,而來救宋國,這是我方理曲而楚國理直,楚軍士氣就旺盛,不可認為他們已經疲勞不堪。如果我方做到以國君避開臣子,而楚軍還不撤退,那就是他們理曲了。」於是晉軍就撤退九十里,避開楚軍。楚軍將士都主張停止戰事,子玉不肯。到了城濮,果然發生了戰爭,結果楚軍被打得大敗。君子評論說:「這是善於以德義來勸說君主。」
晉文公因流亡時鄭文公對他不按禮節接待,就用與討伐偷看他肋骨的曹共公同樣的罪名,攻打鄭國,命令鄭國拆除城上的矮牆。
鄭國用名貴的寶物來乞和,晉文公不答應,說:「你們把叔詹交出來,我就退兵。」叔詹請求前往,鄭文公不答應,叔詹再三請求說:「用我一個人可以救百姓,安國家,君主何必對小臣如此愛惜呢?」鄭文公只好將叔詹交給了晉國,晉文公下令將叔詹處以烹刑。叔詹說:「我希望把話說完而死,那是我的心愿。」晉文公同意聽他陳辭。叔詹說:「上天把災禍降給鄭國,使我們的國君放縱得如同曹共公偷看肋骨的事那樣,拋棄了禮儀,違背了宗親關係。我勸阻說:『不可以這樣。晉公子十分賢明,他的左右隨從都具有做卿的才幹,如果一旦返國即位,必然得志成為諸侯的盟主,那末鄭國的大禍將無法解除。』今天大禍果然到來了。我當初尊重公子的賢明,預先覺察到禍患而加以遏制,這是明智。現在不避個人的犧牲,挽救國家,這是忠貞。」說罷便去就刑,用手抓住鼎耳大聲呼喊:「從今以後,忠心耿耿事奉君主的人,都要落得和我叔詹一樣的下場。」晉文公於是下令不殺叔詹,待以厚禮,將他送還了鄭國。鄭文公因此任命叔詹為將軍。
晉國鬧饑荒,文公問箕鄭說:「用什麼來救饑荒?」箕鄭回答說:「要守信用。」文公問:「怎樣才能守信用?」箕鄭回答說:「國君之心要講信用,尊卑名分上要講信用,實施政令要講信用,安排民事要講信用。」文公說:「究竟該怎麼樣做呢?」回答說:「在國君的心裡講信用,那善惡就不會混淆。在百官尊卑名分上講信用,那上下就不會侵犯。在實施政令上講信用,那就不會誤時廢功,在安排民事上講信用,那百姓從業就各得其所。這樣一來,百姓了解國君的心,即使貧困也不害怕,富裕的拿出收藏的財物用來賑濟,如同往自己家裡送一樣,那又怎麼會窮困匱乏呢?」文公便任箕鄭為箕地大夫。等到清原閱兵的時候,晉國建立五個軍,晉文公讓箕鄭擔任新上軍的副將。
城濮之戰前,晉文公問趙衰誰可擔任元帥,趙衰回答說:「郤縠可以。他已經五十歲了,還堅持學習,而且更加重視。先王制定的法規典籍,是道德信義的寶庫。道德和信義,是人民的根本。能夠重視的人,是不會忘記者百姓的。請讓郤縠擔任此項職務。」文公採納了趙衰的建議。文公又任命趙衰為卿,趙衰推辭說:「欒枝這個人忠貞謹慎,先軫足智多謀,胥臣見聞很廣,都可以擔任輔佐,小臣不如他們。」於是文公任命欒枝統帥下軍,由先軫為副將輔助他。後來攻取五鹿,便是出於先軫的計謀。郤縠死後,又派先軫接替他任中軍統帥。由胥臣擔任下軍副將。
文公又讓趙衰任下卿,趙衰推辭說:「三樁有功德的事情,都是狐偃出的計謀。用德行來治理人民,成效十分顯著,不可不任用他。」文公便任命狐偃為下卿,狐偃推辭說:「狐毛的智慧超過小臣,他的年齡又比我大。狐毛如果不在其位,小臣不敢接受此項任命。」文公於是派狐毛統帥上軍,由狐偃為副將輔助他。
狐毛死後,文公派趙衰代替他任上軍統帥,趙衰又推辭說:「在城濮之戰中,先且居輔佐治軍幹得很好,有軍功的應當得到獎賞,以正道幫助君王的應當得到獎賞,能完成自己職責的應當得到獎賞。先且居有這樣三種應當得到的獎賞,不可不加重用。而且像我這樣的人,箕鄭、胥嬰、先都等都還在。」文公於是派先且居統帥上軍。文公說:「趙衰三次辭讓,他所推讓的,都是些國家得力的捍衛者。廢除辭讓,便是廢除德行。」因為趙衰的緣故,文公在清原地方舉行閱兵,把原來的三軍擴充為五軍。任命趙衰擔任新上軍的統帥,由箕鄭為副將輔助他;胥嬰擔任新下軍的統帥,由先都為副將輔助他。狐偃死後,蒲城伯先且居請求委派副將,文公說:「趙衰三次推讓,都不失禮義。謙讓是為了推薦賢人,禮義是為了推廣道德。推廣道德,賢才就來了,那國家還有什麼可憂慮的呢!請讓趙衰跟您在一起。」於是,晉文公便派趙衰擔任上軍的副將。
晉文公向臼季學習讀書,苦讀了三天,說:「書上所說的我一點點也做不到,但知識見聞卻增多了。」臼季回答說:「那麼,拿這些知識見聞去讓有才能的人來實行,豈不勝過沒有學習之時嗎?」>
晉文公對郭偃說:「開始當君主的時候,我以為治理國家很容易,現在才知道是很困難的。」郭偃回答說:「您以為容易,那麼困難就要來了。您以為艱難,那麼容易也就快來到了。」
晉文公問胥臣說:「我想叫陽處父做歡的老師來教育他,能教育好嗎?」胥臣回答說:「這主要取決於歡。直胸的殘疾人不能讓他俯身,駝背不能讓他仰頭,小種人不能讓他舉重物,矮子不能讓他攀高,瞎子不能讓他看東西,啞巴不能讓他說話,聾子不能讓他聽音,糊塗人不能讓他出主意。本質好而又有賢良的人教導,就可以期待他有所成就。如果本質邪惡,教育他也聽不進去,怎麼能使他為善呢!我聽說,以前周文王的母親懷孕時身體沒有變化,生產時就像小便的時候在廁所里一樣容易,沒有任何痛苦生下文王。文王不讓母親增添憂慮,無需保傅多操心思,未讓師長感到煩擾,事奉父王不讓他生氣,對兩個弟弟虢仲和虢叔很友愛,對兩個兒子大蔡和小蔡很慈惠,為自己的妻子大姒做出榜樣,與同宗的兄弟也很親近。《詩經》上說:「為自己的妻子做出表率,進而及於兄弟,以此來治理家庭和國家。」這樣就能任用天下的賢良之士。到他即位之後,有事諮詢掌管山澤的八虞,與虢仲、虢叔兩兄弟商量,聽取閎夭、南宮括的意見,咨訪蔡公、原公、辛甲、尹佚四位太史,再加上有周文公、邵康公、畢公和榮公的幫助,從而讓百神安寧,使萬民安樂。因此《詩經》上說:『文王孝敬祖廟裡的先公,神靈都沒有怨恨。』從這看來,那麼周文王的成功就不單單是教誨的作用了。」
晉文公說:「這樣說來,那教育就沒有用了嗎?」胥臣回答說:「要文采幹什麼呢,就是為了使本質更加美好。所以人生下來就要學習,不學習就不能進入正道。」文公說:「那對先前所說的八種殘疾人怎麼辦呢?」胥臣回答說:「這就要看自身長處因材而用了,駝背的讓他俯身敲鐘,直胸的讓他戴上玉磬,矮子讓他表演雜技,瞎子讓他演奏音樂,聾子讓他掌管燒火。糊塗的、啞巴和小種人,自身沒有可利用的正材,就讓他們去充實邊遠的地區。教育,就是根據他內在的性能、本質加以因勢利導,就像河川有它的源頭,迎到入海口,匯入大海任意奔流。」
晉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就想使用他的人民進行征戰,子犯說:「人民還不懂得大義,何不把周天子護送回去,以此顯示大義呢?」於是文公就派軍隊護送周襄王返回周都。文公又問:「現在可以了吧?」子犯回答說:「人民還不懂得信用,何不攻打原國,以此顯示信用呢?」於是文公就出兵征伐原國,示信於民。文公又問:「現在可以了吧?」子犯回答說:「人民還不懂得禮儀,何不舉行一次大規模的閱兵,整頓軍隊,崇禮尚武,來顯示禮儀呢?」於是文公便在被廬舉行大規模的閱兵,建立了上、中、下三軍。任命郤縠統帥中軍,執掌國家大政,由郤溱輔佐他。子犯這時才說:「現在可以興兵征伐了。」於是文公便發兵攻打曹、衛兩國,迫使楚國撤走戍守齊國谷地的楚軍,解救了楚軍對宋國的包圍,在城濮之戰中打敗了楚國軍隊,於是稱霸諸侯。
參考來源
參考資料
- ↑ 《國語·卷七·晉語一》 - 古籍備覽- 國學書苑,國學網 , 2022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