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冬天(乔晖)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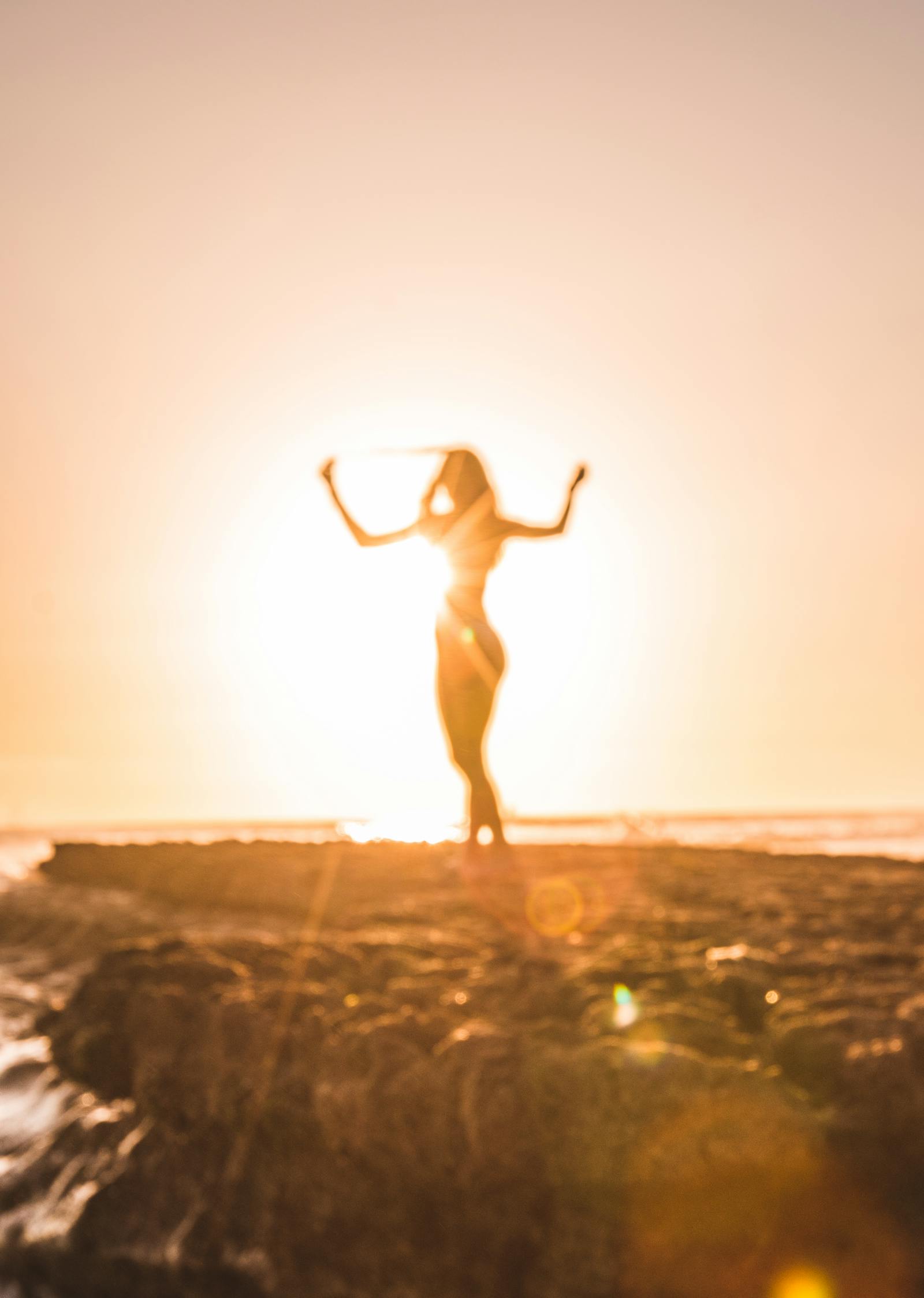 |
《陕北的冬天》是中国当代作家乔晖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陕北的冬天
陕北的冬天是比较漫长的,从每年的十一月上旬立冬开始,到下年3月上旬的惊蛰结束,4个月里包含了小雪、大雪、小寒、大寒等9个节气,还有元旦、春节和元宵节三个重要的节日。
记得小时候的冬天,天气特别寒冷。灰蒙蒙的天上挂着一层乌云,呼啸的西北风,裹挟着砂砾,从山山峁峁、沟沟坎坎、坡坡洼洼肆无忌惮地刮过,直立向天的树梢,发出“嗦嗦嗦”的响声,匍匐在地上的枯草,也发出痛苦的呻吟。小孩穿着臃肿的棉袄棉裤和羊毛织的袜子,踏着一双没后跟的布鞋,脚和手被冻得裂了口子,鼻涕像两条虫子挂在鼻孔进进出出,有时能“锁”住嘴;放羊人穿着没有布面的山羊或绵羊皮袄,扎紧腰里的麻绳,怀里抱着一只拦羊的铁铲铲,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院子里的公鸡带着一群母鸡,随风摇摆,还不忘觅食;小河沟和大河沟的水,被冻成了冰川,静静地躺卧在沟底;蜿蜒起伏连绵不断的黄土大山,无可奈何地互相对视着,默默无语……
不管怎么说,冬天来了,冬闲就给了农民喘息的机会。经过了春播、夏锄和秋收的辛苦劳作,进入了天寒地冻的冬天,农民就不再下地干活了。太阳终于艰难地钻出了云层,给大地洒下了一缕缕金光。老农们不约而同地来到避风的阳崖崖坡跟下,蹲成一行行,悠闲地眯着眼睛晒太阳,“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一锅子抽完,就在鞋底子或鞋帮子上磕掉烟斗里的烟灰,再装上一锅子旱烟继续“吧嗒”。他们边抽烟边拉话,无拘无束天南海北,想起啥就拉啥。这时,能谝闲传胡吹冒聊口齿伶俐的人,就开了腔,或是一本正经地说国家大事,或是眉飞色舞瞎编排本村或邻村的绯闻轶事,瞎说溜道完了,不忘再说一串黄段子,惹得大伙儿哈哈大笑,一张张额头上深沟似的皱纹舒展了许多。
冬天里,最热闹的是打平伙。吃完午饭,闲来无事,村民们喜欢串门子,有时就集中到了一个村户家。脱鞋上炕,盘腿坐在炕上,主家端出来半脸盆葵花籽,他们边抽烟边嗑瓜子边聊天。有人提议:“今天基本到全了,咱们打平伙喝一场。”众人赞同。于是,生产队长就指派两个青壮年人去羊群里挑选一只对牙或四个牙的山羊羯子,拉回来杀了,剥皮秤肉,剁肉下锅。吃肉的人将均摊的钱交给会计保管并上账,年终决算分红,做肉这家人因为贴了调料贴了柴禾,就白吃一份不摊钱。羊肉下到一口大铁锅里,这家的婆姨就一会儿“噗嗤噗嗤”地拉着风箱,一会儿又站起来,把锅里的血沫子一点一点的撇出来,再把生姜、花椒、葱段、咸盐倒进锅里,继续拉风箱烧火。炕上的村民们有的打扑克,有的折牛腿(也叫掀花花),赌注都不大,每局输赢的分数都记在纸上,最后把输者的钱集中起来,指定两个人去商店买几瓶烧酒几包香烟。一会儿,清炖羊肉的浓浓香味,就弥漫了窑洞的角角落落,大约过了三个多小时,羊肉就熟了。生产队长就把锅里的羊肉一勺子一勺子舀在每个洋瓷碗里,一人一大碗。大伙儿围坐在炕桌旁或地上的条桌前,一边吃肉一边猜拳喝酒,炕上的玩“石头剪子布”,地上的玩“杠子打老虎”,吆天嗨地不亦乐乎,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震得窑洞窗格格上的麻纸哗啦啦直响。好酒不服输的人,喝得面红耳赤脖筋突跳,粗话不绝于耳,逗得众人哈哈大笑,把陕北人粗犷豪放的性格抖露得淋漓尽致。也有细心的男人,怕人家骂他“软耳根”,看见别人不注意,把分到的羊肉悄悄地端回到家里,婆姨就笑眯眯地接住羊肉,做一锅羊肉烩菜,蒸一锅黄米干饭,一家人美滋滋地吃一顿。
徬晚,一疙瘩一疙瘩的云彩聚集到一块,像一把巨大的黑伞,遮罩住了整个蓝天。鹅毛大雪沸沸扬扬飘飘洒洒,轻盈地落在地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拉开门,才知道大雪下了一夜,现在还有零零星星的雪花在头顶飘荡,院子的积雪平展展的足有七八寸厚,踩在雪上,雪淹没了鞋子,钻进鞋里,冰凉冰凉,地上留下一串串深深的雪坑坑。从鼻孔里出去的气,立马就变成一小团的雾,冻得人浑身哆嗦、打颤。大雪覆盖了所有的山所有的地所有的路,黄土地变了模样,变成洁白的世界。农民们拿出铁锹,铲起院里的积雪,密密麻麻的雪堆,堆满了院子。中午时分,乌云慢慢撕开了口子,阳光从云缝里挤出来射向大地,照在雪上,一眼望去有点刺眼晕目。下午,雪堆稍有融化,农民们就用铁锨拍拍打打,把雪堆紧踏实,一夜之间,雪堆就凝固了,人们启起雪堆,填满几个水窖,再把院子里的余雪,倒到菜园子或果树园子。
一场大雪,大约过了一周才慢慢地融化,这就饿坏了麻雀和鸽子。只见一群麻雀和一群鸽子,急不可待地飞落在场上的糜谷垛子下边,用小爪爪抛开垛子底下的糜谷草叶和苡子,贪婪地寻觅充饥的食物。这时,是扣麻雀和鸽子的最好时间。
我和邻居的小伙伴在家里找出两个筛草筛粮食用的筛子和两条绳子,急匆匆地来到场上。我们在两根木棍棍上拴上绳子,用木棍棍顶在筛子的边沿,分别把两个筛子安放在谷垛和糜垛的下边,两条长长的绳子分别攥在我俩的手心,我们躲在场堎堎下,不动声色地探头张望。不一会儿,目标就进入视线,只见一群麻雀和一群鸽子落在糜谷垛子下边,“叽叽喳喳”地开始“美餐”,筛子下边的麻雀和鸽子越聚越多,我们互相使了个眼色,一同拉了一下绳子,两个筛子同时倒地,惊得筛子外的麻雀和鸽子“扑棱棱”地飞向天空。我们小心翼翼地把筛子揭开一点手能伸进去的缝隙,一把一把地抓住麻雀,一个一个地逮住鸽子,然后装进两个麻袋里。饥饿的麻雀和鸽子,不长记性,应了那句“饥不择食”和“鸟为食亡”的古话,一会儿就又飞回来了。我们用同样的办法,又扣了两次,麻雀和鸽子装了两半麻袋。我们在打谷场的周围拔了一些干蒿柴,抓出十来只麻雀,权当烧烤的野餐,吃得两嘴留下两个黑圈圈,互相对视一笑,满载而归。
回到家里,炕上的大花猫,两眼直直地窥视着麻袋,发出“咪~咪~”的叫声。我把麻袋里的麻雀抓出一只,在猫的面前一晃动,说是迟那是快,大花猫一跃而起,一嘴就叼走了麻雀。吃完一只再吃一只,吃饱后懒洋洋地卧在热炕上。用开水煺掉麻雀和鸽子毛,开腔倒肚,拾掇干净,一半下锅,一半用细麻绳绳拴在爪子上,挂在背荫的树上冷冻起来。麻雀在开水锅里上下翻腾,我说:“真是煮了一锅麻雀~净嘴无肉。”小伙伴会意地抿嘴一笑……鸽子肉吃起来慢嚼细咽,比鸡肉细嫩、爽口,留在舌齿上的美味久久挥之不去。
可能是全球变暖的原因,现在陕北的冬天没有四十年前冻了,人们穿着保暖内衣和外套就可过冬,再没有见到穿羊毛织的袜子,更没有见过谁的脚和手有冻裂的口子。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打工潮的兴起和移民搬迁,大山深处不少的原始村庄,只有个别老人在守望,有的土窑洞间口塌陷,门窗破落,满院的黄蒿野草有半人多高,脑畔上的烟囱也没有袅袅炊烟,打工族冬天也有活干了,往往是一年四季春节才能回家团聚。腰包鼓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打平伙变成了下馆子,想吃啥就吃啥。下雪天一改过去给水窖里收雪,变为现在下雪时,到雪地里赏雪、堆雪人。
白驹过隙,又逢冬季。好想好想在老家的窑洞里,再打一次平伙。大雪过后,在打谷场上,再扣一次麻雀…… [1]
作者简介
乔晖,陕西定边县人,中国电信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