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漂流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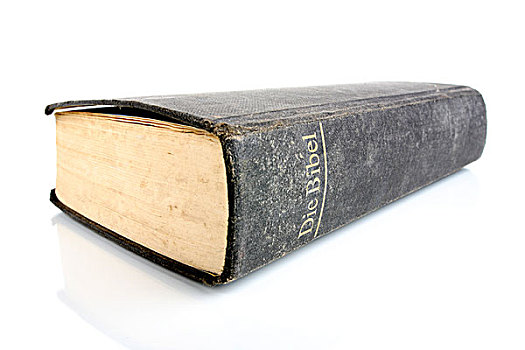 |
旷野漂流,外文名:WILDERNESS OF WANDERING,基督教圣经专名。
基督教[1]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三大宗教。但是,基督教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方面,都堪称世界第一大宗教[2]。基督教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有着极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和深远影响。
简介
Ⅰ 范围
以色列人自从出埃及、过芦苇海(Sea of Reeds)(出十四10-十五27)开始,到最后越过以东和摩押,抵达约但河岸(民廿起)为止,在经过之地耗费了不少年日。这片土地包括: (1) 西乃半岛:两侧被苏彝士湾与亚喀巴湾包围,北面是一条连接埃及至巴勒斯坦的“非利士地的道路”,这尘埃路把此地与地中海分开: (2) 狭长的亚拉巴裂谷:由死海向南伸展,至亚喀巴湾: (3) 别是巴以南的寻的旷野。
Ⅱ 天然特征
由埃及经“非利士地的道路”到拉非亚(Raphia)和迦萨的路,大玫上与地中海沿岸平行,沿途经过一个贫瘠沙漠──*书珥旷野──的北边,这旷野是在现今的苏彝士运河和亚里士河谷(Wadi el-`Arish,*埃及河)之间;上述的路逐渐进入耕地,这在亚里士与迦萨之间的一段更为明显(*南地;参 A. H. Gardiner, JEA 6, 1920,页114-5; C. S. Jarvis, Yesterday and Today in Sinai, 1931,页107)。在沿岸之路以南,相距约三十至六十公里,是“书珥旷野之路”,由埃及至加低斯地区,再往东北,抵达别是巴。从这路向南走,在蒂(Et-Tih)这石灰石高原上,渐渐有更多山丘和河谷出现,蒂高原的范围是以连结苏彝士湾及亚喀巴湾两源头的线作为“底线”,呈巨型半圆形的往北进入西乃半岛。横过高原到达亚喀巴湾的路是古代一条贸易经商的路线。高原南面的三角形地带,是由花岗岩、片麻岩和其他坚硬结晶岩石组成的山脉,传统认为是西乃山的山岭亦在其中,有些山峰更高达二千公尺。这地区在西北和东北角落,是沙岩土质的山丘,与上述的石灰石高原隔开;这些山丘含有铜矿和绿松石矿。蒂石灰石高原在东面与南地(尼革)的南面接连,后者是一大片杂乱的岩石及河谷,东临死海和亚喀巴湾之间的亚拉巴裂谷。
沿着西岸由苏彝士地区向下走一天的路程到马卡哈(Merkhah),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井或泉出现,一般来说,地下水位与满布碎石的地面十分接近。河谷通常长有少量的某种植物;若河流差不多终年有水,植物便相应地生长茂盛,菲兰河谷(Wadi Feiran,西乃最好的绿洲)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冬天的“雨季”(最长可达二十日)是有薄雾、浓雾及露珠的日子。
以前,垂丝柳和什亭木的丛林经常被人砍伐,用作柴炭;十九世纪年间,什亭木且陆续不断出口,输往埃及(Stanley, Sinai and Palestine, 1905版,页25)。由此看来,古时西乃半岛的河谷可能长有更茂盛的植物,显示雨量较多;但从古至今,当地的气候似以乎没有重大的变化。
Ⅲ 漂流的路线
昔日以色列人由芦苇海(位于奎塔拉 [Qantara] 与苏彝士湾之间;*红海)到摩押边境,所采用的确实路线仍属推测,因为亚拉伯语对西乃半岛各地的名称来自晚期,属描述性质,变化颇大,而以色列人在旷野曾经停留的地方,其名字差不多都没有保存下来。以色列人为多个停驻地所起的名字,都与他们旅程上发生的事件有关,例如,基博罗哈他瓦的意思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民十一34),但他们中间没有人留下来在那地方定居,遂不能使这些名字传流后世。再者,有关今日西乃山(慕萨山 [Gebel Musa] 及其四周)的传说,只追溯到初期教会头数百年,再古的考据便付诸阙如;这点本身不能证明有关传说是错误的,但我们却也不能肯定它们的真确性。传统声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肯定有其可能性。学者一般认为,他们离开*书珥旷野后,即沿着西乃半岛西岸地带向南前进;学者通常主张玛拉和以琳分别是今日哈哇喇泉(`Ain Hawarah)和加兰德河谷(Wadi Gharandel)。以色列人离开以琳后(出十六1),“安营在红海(yam su^p{)”(民卅三10的希伯来说法)旁边;红海在此是指芦苇海,或引申指苏彝士湾(参*红海)。这点清楚显示以色列人并没有向北走(非利士人的道路),而是留在西乃半岛的西面。亚喀巴湾相距太远,不会是这段经文所说的“红海”(yam su^p{)。经过一段时间,以色列人在脱加(Dophkah)安营。有些学者认为这地名的意思是“冶炼厂”(G. E. Wright, Biblical Archaeology, 1957,页64;Wright and Filson, Westminster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Bible, 1957版,页39),所以此地是处于埃及的矿产中心塞拉毕卡底呣(Serabit el-Khadim)这区域内。有关这地区开采铜矿和绿松石的情况,见:卢卡斯(Lucas),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1962,页202-5、404-5;车尼,加德纳尔及皮特(J. C%erny*, A. H. Gardiner and T. E. Peet), Inscriptions of Sinai, 2, 1955,页5-8。
由于以色列人是在亚笔月(即三月期间,参*埃及的十灾)离开埃及(出十三4),一个月后(即在四月期间)再由以琳起行(出十六1),而埃及〔采矿〕的远征队只在一月至三月间(很少在三月之后)探访这地区,且不会长驻矿场(参 Petrie, Researches in Sinai, 1906,页169),所以,以色列人不会在这地区遇见他们。然而,横跨西乃中南部的沙岩地带盛产金属矿物(这点且有利“以色列人采南路进迦南”之说),所以脱加可以是这地区内任何采铜之处。有学者认为利非订就是菲兰河谷,或是雷法伊德河谷(Wadi Refayid),而西乃山则被一些人鉴别为慕萨山峰(或是靠近菲兰的塞巴山〔Mt Serbal〕,但可能性较低)。见:鲁宾逊(Robinson),莱斯亚斯(Lepsius),斯坦(Stanley)及帕尔默(Palmer)的著作(见下面书目)。越过西乃山,东岸的达哈(Dhahab)可能是底撒哈(Di-zahab,申一1;持这意见的有 Y. Aharoni, Antiquity and Survival, 2. 2/3, 1957,页289-90,图7);若是这样,在另一条路上的户特拉(Huderah)就不大可能是民十一35和卅三17-8的哈洗录。下一个可确定的地点是加低斯巴尼亚(*加低斯),它是在寻旷野和巴兰旷野(民十二16,十三26)的边缘,位于奎戴拉得泉(`Ain Qudeirat),或奎戴斯泉(`Ain Qudeis)及其四周地区,包括奎戴拉得泉在内。另一个定点是亚喀巴湾顶端的以旬迦别(民卅三35-36)。
有关地开口吞没可拉、大坍和亚比兰的事件(民十六),霍尔特(G. Hort)提供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解释(Australian Biblical Review 7, 1959,页2-26,特别是19-26)。她认为这件事是在死海与亚喀巴湾中间的亚拉巴裂谷发生。这里有一种名叫 kewirs 的泥滩:一层坚硬的黏土,外层覆盖着多层的硬盐和半干泥,总共厚三十公分,在深厚的泥泞及软泥之上逐渐形成。当外层坚硬时,人可以安然地在上面行走,但不断上升的湿度(特别是暴风雨期间),终会使坚硬的表层软化,整片地完全变成胶泥。大坍、亚比兰和可拉,并支持他们的人,离开中央营地后,可能就是站在这种看似坚硬的泥滩上。摩西有多年在西乃和米甸生活的经验(出二-四),可能认识这种现象,但以色列人却不晓得。当暴风雨临近时,他看出危险,于是召集以色列人离开叛徒的帐棚。这时泥土的表层软化裂开,把一班背叛者、他们的家眷和财物,完全吞下去。暴风雨接踵而至,那二百五十个拿着香炉的人被闪电击中──被从耶和华而来的火烧灭了。
霍尔特女士认为这件事发生于加低斯巴尼亚,所以加低斯应该位于亚拉巴。但是,有一些理由可以支持*加低斯位于奎戴斯泉和奎戴拉得泉之说;事实上,民十六并没有声明可拉、大坍和亚比兰的背叛是在加低斯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读来合理且符合上述自然现象的,是唯独民十六对这两次背叛事件及当事人可怕结局的完整记载;至于从惯常文件分析推想出来的所谓资料来源,却只引至文离破碎的图画,与所知的事实并不相符。
民卅三10-35的一大串地名,是以色列人卅八年漂流经过的地方,今日地点已不详。他们绕过以东之后,所采的确实路线(民廿22起,廿一,卅三38-44),今日也难以稽考。在这长期旅程中,一些事件的发生反映了当地的自然现象。两次击石出水的现象(出十七1-7;民廿2-13),反映西乃石灰石贮水的特性:一位军士偶然用铲子打了一下这种岩石的表面,便有大量的水涌流出来!见:杰菲斯(Jarvis),Yesterday and Today in Sinai, 1931,页174-5。民廿一16-18(参:创廿六19)的记载中挖井一事,反映了今人所知在西乃、南地、外约但多个地区出现地下水的情况(见上列参考资料,及 N. Glueck, Rivers in the Desert, 1959,页22)。按一些人的解释,捕取鹌鹑一事(出十六13;民十一31-35)显示,出埃及的行程必定是沿地中海北行的路线(如 Jarvis,上引书,页169-70;参 J. Gray, VT 4, 1954,页148-54;依循他看法的有 J. Bright, A History of Israel, 1960,页114;另参 G. E. Wright, Biblical Archaeology, 1957,页65)。但神明明禁止以色列人走这条路(出十三17-18),更何况鹌鹑只在秋天和清晨由欧洲飞达西乃的地中海沿岸,而以色列人却是在春天的傍晚发现它们,当时是亚笔月期间或稍后,即三月(出十六13),另一次是相距一年零一个月之后的时间(民十11,十一31)。这两个理由排除了以色列人在这两次事件中沿地中海岸边行走的说法,及直接显示他们采用了沿苏彝士湾经“西乃山”至亚喀巴湾的南行路线。鹌鹑是在春天返回欧洲,于傍晚时分飞越苏彝士湾和亚喀巴湾的顶端,而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个季节两次发现它们(Lucas, The Route of the Exodus, 1938,页58-63及参考资料,以及页81,他忽略苏彝士湾而过分强调亚喀巴湾)。
一个少数人抱持的观点,认为以色列人较直接地横越西乃半岛,抵达亚喀巴湾的顶端,而西乃山位于米甸。拥护这观点的学者中,一位佼佼者是卢卡斯(Lucas, The Route of the Exodus, 1938),但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把一些现象归因于实际上不存在的活火山。然而,比起其他看法,这论点也不乏地形上的难题,而且完全不能解释在基督徒时期突起的传说为何是跟今日名叫西乃的半岛拉上关系,而不是跟米甸或亚拉伯西北部拉上关系。
有关出埃及记至民数记、民数记卅三及申命记中以色列漂流路线与停留地方的资料,一个上乘的比较图表,见:戴维斯及格曼(J. D. Davis and H. S. Gehman), WDB,页638-9;文学背景方面,参:戴卫斯(G. I. Davies),TynB 25, 1974,页46-81;有关青铜器时代西乃的遗址,参:汤普森(T. L. Thompson),The Settlement of Sinai and the Negev in The Bronze Age, 1975。
Ⅳ 以色列人的数目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这还不包括妇人、孩子及其他闲杂人;此外,在西乃进行的人口统计中,不计利未支派在内,其他支派共有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名年过二十、能出去打仗的男人(民二32)。一般认为,这些数字意味当时以色列人的总人口──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超过二百万。圣经的资料显示(实地勘查也指向同一结论),西乃稀少的资源本身不足以养活这么庞大的人群:他们主要的粮食是神所赐下的*吗哪(出十六;参3-4、35节)。以色列人在漂流的日子,虽然有时几乎缺水(如:在利非订,出十七1;在加低斯,民廿2),但从不曾完全匮乏(申二7)。无论如何,他们很快学会如何在水源不足的环境下维持生命,就像鲁宾逊(Robinson)在西乃的导游,他能够不喝水,单靠骆驼奶在西乃生存十四天;又像羊和骆驼,只要它们刚吃过新鲜的青草,接着下来虽然没有水,有时候仍然能够生存三至四个月之久(E. Robinson, Biblical Researches, 1, 1841版,页221)。
再者,有些想法是完全误导人的,例如:以色列人“四人一排”的形成多个很长的队伍在西乃走来走去,或说以色列人在每一处安营的地方,都是整体地集中在某条很小的河谷内扎营。他们乃是按支派、宗族分布,在多类互相毗邻的河谷分散扎营;他们携带约柜和会幕(每次起行时都携作行李)离开西乃后,会幕每次放置的地点便成为各支派扎营的焦点,像民二所描述的。在西乃不同的地区,地下水的水位都很接近地面;因此,分散前扎营的以色列人往往只要挖掘一些小坑,就可取水,满足些微的需求。参:鲁宾逊(Robinson), Biblical Researches 1, 1841,页100(一般的观察)、129;莱斯亚斯(Lepsius),Letters,等等,1853,页306;柯里利及皮特里(Currelly and Petrie), Researches in Sinai, 1906,页249;卢卡斯(Lucas),The Route of the Exodus, 1938,页68。
历来有不少人尝试解释民一和廿六的人口统计数字、出十二37与卅八24-29的有关数字,以及利未人的数点(民四21-49)与其他的数字(如:民十六49),以便从希伯来文的经文,得出昔日从埃及经西乃到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的适中数目。近期的尝试,见:格拉克(R. E. D. Clark), JTVI 87, 1955,页82-92(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 ~lp 是指“长官”,而不是“一千”);孟德贺尔(G. E. Mendenhall),JBL 77, 1958,页52-66(他以 ~lp 为支派中的分支,代替“一千”的解释),他提到在此之前的处理方法;温南(J. W. Wenham),TynB 18, 1967,页19-53,特别是页27起、35起。没有一种尝试可完全解释所有的数字,但它们提供了几点可能的线索,让我们对旧约一些似乎庞大的数目可有更好的理解。事实上,这些记录,多少有古时的实况为基础;那些看似庞大的数目不是可以绝对否决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另一个解释能够恰当地阐明所有这些数据。(*数目)
Ⅴ 后期的意义
从神学的角度看,旷野时期日后具有两种象征意义:一方面显出神的引导和供应,另一方面显出人类背叛的本性──以色列人成了人类的写照(参:申八15-16,九7;摩二10,五25〔参:徒七40-44〕;何十三5-6;耶二6;结廿10-26、36;诗七十八14-41,九十五8-11〔参:来三7-19〕,一三六16;尼九18-22;徒十三18;林前十3-5等)。
参考文献
- ↑ 宗教文化:什么是基督教,第一星座网,2015-02-05
- ↑ 正确对待宗教信仰寄托与心灵慰藉的社会作用,道客巴巴,2015-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