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火歸一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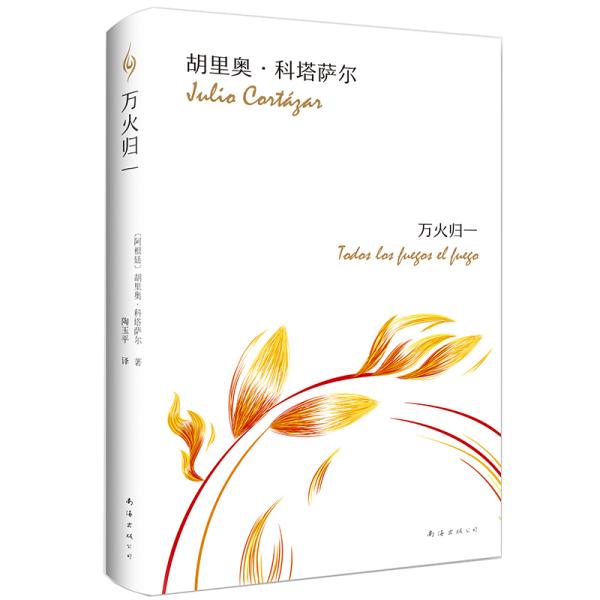 |
內容簡介
在有限逼仄的空間內,將自身的意識和想象發揮到極限。午夜的公路上、飛機的機艙內、冰冷的病房中、玻璃穹頂的天空之下……科塔薩爾的筆下誕生出一個個奇特扭曲、堅韌隱忍的靈魂,他們掙扎着逃脫既定的命運,即便火焰已不可抵擋地團團包圍 。
本書是胡里奧·科塔薩爾短篇小說的集大成之作,收錄有《南方高速》《病人的健康》《會合》《科拉小姐》《正午的海島》《給約翰·霍維爾的指令》《萬火歸一》《另一片天空》八部短篇。小說構思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展開,一如作家往常的風格,隨着情節發展逐漸剝離出失控和荒誕的一面,將現代人在社會生活中不可思議的複雜情緒以超然的手法表現得淋漓盡致。
作者簡介
胡里奧·科塔薩爾阿根廷著名作家,拉丁美洲「文學爆炸」代表人物。1914年生於比利時,在阿根廷長大,1951年移居法國巴黎。著有長篇小說《跳房子》,短篇小說集《遊戲的終結》《萬火歸一》《八面體》《我們如此熱愛格倫達》等。1984年在巴黎病逝。
科塔薩爾被認為是20世紀最具實驗精神的偉大作家。《西語美洲文學史》的作者奧維耶多說:「每當想到科塔薩爾的名字,人們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詞是:迷人。」
原文摘錄
他能做的只有投身於車流,機械地隨着周圍的車輛調整速度,頭腦一片空白。 車流以時速八十公里的速度朝着漸行漸增的燈火駛去,卻沒有人真正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匆忙,為什麼要在夜間公路上置身於陌生的車輛之中,彼此間一無所知,所有人都直直地目視前方,唯有前方。 「你們大家對我太好了,」媽媽說話時帶着柔情,「你們費了那麼多心思,一直不讓我難過。」 羅克舅舅坐在她身旁,快快樂樂地撫摸着她的手,說她在犯傻。佩帕和羅莎假裝在櫥櫃裡找什麼東西,她們明白瑪利亞·勞拉說得對;她們明白了大家在某種程度上一直都知道的事實。 「一直照顧我……」媽媽說道,佩帕緊緊抓住羅莎的手,因為這句話讓一切都恢復了原狀,這漫長而必要的喜劇全盤復原。可卡洛斯站在床前,看着媽媽,仿佛知道她還有什麼話沒說完。 「現在你們可以好好休息了,」媽媽說,「我們不會讓你們再這麼辛苦了。」 羅克舅舅想辯白兩句,可卡洛斯走到他身邊,用力捏了一下他的肩膀。媽媽一點一點陷入了昏睡,最好別去打擾她。 葬禮後的第三天,阿萊杭德羅[小兒子]的最後一封信到了,信里一如既往地問起媽媽和柯萊麗雅姨媽的身體狀況。是羅莎拿到的信,她把信拆開,不假思索地讀了起來,淚水突然湧出,模糊了她的視線,她抬起雙眼,意識到自己在讀信時,心裡想的是怎麼告訴阿萊杭德羅媽媽去世的消息。
書評
胡利奧·科塔薩爾的短篇小說《正午的島嶼》的靈感不過是因為一次普普通通的飛機旅行。中午時間飛機正穿越愛琴海,他坐在舷窗前,看見一片深藍色海中有一個奇妙的小島浮在水面上。那一刻,他產生了一種神奇和非現實的感覺,因為那是一個無名之地,周圍也沒有人知道,然而他恰好就在它的上空,突然有種想到那裡去的渴望。於是,他就成了小說中的乘務員瑪利尼,每天經過這個無名之島的上空,然後在作家的想象中,瑪利尼代替他登上了那個島嶼。提到科塔薩爾的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他的短篇小說中迷人的特質:來源於經驗和現實,但又具有強烈的非現實的幻想意味。
提到科塔薩爾的短篇小說,經常會有人會拿他與博爾赫斯的短篇作比較。他們之間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博爾赫斯的短篇大都是來自於幻想的現象本身,是與現實無關的智力思辨的產物;而科塔薩爾的短篇雖然具有濃重的幻想色彩,但同時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就是說,幻想的東西產生於現實主義的情境,產生於每天的、日常的、普通人身上發生的再平常不過的事件。《南方高速》中一次高速公路上的堵車事件;《病人的健康》中兒女們為了避免母親的喪子之痛撒下的善意謊言;《克拉小姐》中護士與孩子病人之間的微妙的感情糾葛;《給約翰·豪威爾的指令》中一個秋日的午後去劇院看戲的經歷,等等。但科塔薩爾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從這種普通生活場景中抽離出一種非常態的、例外的、荒誕甚至神奇的小說特質。
接下來就是見證科塔薩爾小說中的奇蹟時刻:回巴黎的高速公路上堵車了,科塔薩爾巧妙寫下這個普通場景時特意避開了書寫時間,仿佛時間靜止了,前面的交通意外永遠沒有解決的可能,被隔絕在車裡的人不得不在一個靜止的時間裡重新排列組合,像人類伊始踏入社會,他們選出領導者,搜集、交換和分配食物、水等資源。他們組合成小團隊,成員有醫生、看護、修女,處理突發事件者,應付外來入侵者,有條不紊地安排着被隔絕在高速公路上的「日常生活」,直到有一天公路莫名其妙的流通了。他們在高速公路上待了多久?為何堵車?又為何通行?我們都不知道,科塔薩爾也不知道。《南方高速》仿佛張愛玲筆下的《封鎖》,時間打了一個盹,非常態時刻下的秩序井然又恢復了常態的混亂,各奔東西。年邁多病的母親最疼愛的小兒子阿萊杭德羅突發車禍死亡,孝順的子女為了對母親隱瞞這個壞消息,他們特意製造了阿萊杭德羅遠在巴西工作的假象,為了做得逼真,更要求那邊的朋友以兒子的名義寫信到家,一直到母親去世。《病人的健康》中所有的鋪墊都是為了寫出小說中最後一個神奇的句子,媽媽去世後,兒女們收到了從巴西寄來的最後一封信,「信是羅莎接到的,她打開信,不假思索地讀了起來,突然她抬起頭,因為淚水已經模糊了她的眼睛,她意識到自己在讀信的同時正在考慮該怎樣告訴阿萊杭德羅母親去世的消息。」
《給約翰·豪威爾的指令》更是荒誕味十足。瑞斯在一個秋日午後百無聊賴走進一家劇院,在幕間休息的時候被劇院的工作人員邀請到後台,隨後就在脅迫下成了他剛剛還在觀看的戲劇的男主角約翰·豪威爾。他剛剛入戲演到了第三幕又被莫名其妙地轟下了舞台,豪威爾換成了其他人,他又變成了另一個自己的觀眾。結尾的部分中,他和另一個豪威爾似乎遭到了追殺,逃離了劇院。至於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讀者和書中的人物一樣覺得莫名其妙。科塔薩爾給我們開了一個卡夫卡式的玩笑。對,這個迷人的短篇很容易讓人想起卡夫卡的風格。把握真實世界曾經是小說定義的一部分,但是有沒有一種辦法即能把握住它,同時又沉湎於令人銷魂的幻想遊戲呢?即能嚴肅認真地分析世界,同時又不負責任地在夢幻的遊樂中自由馳騁呢?「卡夫卡解決了這一難題,」米蘭·昆德拉說,「卡夫卡在真實性的高牆上打開了缺口,許多別的作家緊跟着他各以各的方式通過了這一缺口。」這其中就有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卡洛斯·富恩特斯,當然還有胡利奧·科塔薩爾,他們都是拉丁美洲文學「爆炸」中的代表性人物。
關於拉丁美洲文學與歐洲文學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地理上的距離使得拉丁美洲的作家遠離區域性的環境,從而可以讓他們意識到歐洲文學的大環境;但在這種歐洲文學環境的映照下又凸顯拉丁美洲小說的獨特的美學價值,即一種形式上的新穎性。如果說拉丁美洲作家群里有一個很好體現了他們與歐洲文學之間這種複雜難言微妙關係的作家,非科塔薩爾莫屬。這一方面與他早年在法國的流亡經歷有關,另一方面也體現在他的多產以及對短篇小說的形式和結構極富探索的革命精神上。從《萬火歸一》這部短片小說集中我們可以管中窺豹,八篇小說中每一篇都頗具新穎,毫無重複累贅之感。尤其值得一提的《克拉小姐》這樣的名篇,人物之間基本沒有任何直接場景設置和對話情境,只有各自的心理活動,帶動整個故事的發展。這種完全靠語言和句子本身的起承轉合完成的小說不但實現了一種「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新型小說形式,而且體現了科塔薩爾在語言上的無比簡約的風格和精湛技巧。借用米蘭·昆德拉評價卡夫卡、穆齊爾、布洛赫等人的話說:「他們都是小說的詩人。也就是說:熱愛小說的形式與新穎性;關注每一個詞和每一個句子的力量;受到試圖穿越『現實主義』邊界的想象力的誘惑;……完全專注於現實世界。」
胡利奧·科塔薩爾無疑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小說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