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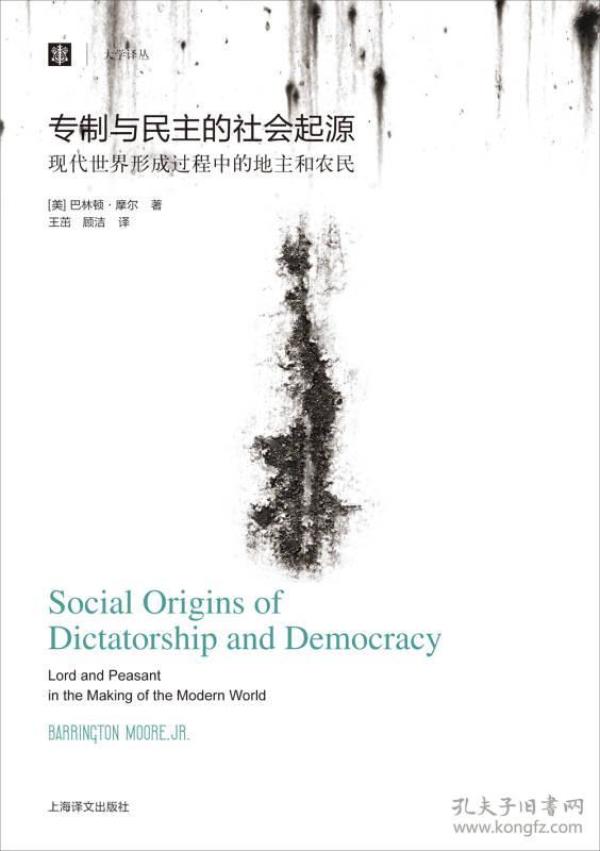 |
內容簡介
《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的作者是美國當代知名社會學和歷史學專家巴林頓·摩爾,此書是一部視野寬廣的史學論著。本書是對西方正統現代化理論的一個重大挑戰,抨擊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是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的惟一道路和最終歸宿的西方傳統觀點,並在揭示大量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指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歷史環境中結出的果實,而通向現代社會的歷史道路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體制形態是形形式式的。此書1966年問世後,即在歐美文化思想界引起普遍反響,標誌着當時美國社會思潮的重大轉折,此書一經出版,即成為西方學術經典,被譽為"對人類社會和歷史所進行的重大探索",作者也因此榮膺伍德羅·威爾遜獎和麥基弗獎。
作者簡介
摩爾·巴林頓(Moore,Barrington Jr. , 1913-2005),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 1913 年出生於華盛頓。大學時代,曾就讀於威廉學院和耶魯大學。畢業後執教於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並在哈佛的俄國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工作。摩爾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多產作家,他先後出版過《蘇聯政治》(1950 )、《政治權力與社會理論》(論文集,1958 )、《專制和民主的社會起源》(1966 )、《人類苦難淵源的反思》 (1972) 和《非正義》(1978 )等著作。其中,《專制和民主的社會起源》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影響的著作。該書出版後立即風靡美文化思想界,作者因此而榮獲伍德羅·威爾遜獎(1968 )和麥基弗獎( 1969 )。儘管該書出版已有 30 多年,但仍暢銷不衰,並獲得西方學術經典的炫目位置。
原文摘錄
在日本,現代世界的到來確實促使了農業產量的提高,但是這種提高主要形成了一個小業主階層,他們利用了混合在一起的資本主義機制和封建機制,從農民那裡榨取稻米。大多數農民的生存狀況更接近於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當然並沒有像中國和印度所發生的那樣,時不時面臨大範圍饑荒的絕境。。。這一新興地主階級既沒有發展出什麼文化藝術,也沒有像鄉村早期統治者那樣確保鄉村的安全,事實上它所能給予的不過是狂熱的原法西斯主義者情緒而已。一個滔滔不絕吹噓自己對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的階級通常所走的道路其實就是一條威脅人類文明的道路。 在15世紀的動亂年代裡,土地除了它的經濟價值之外,仍然具有某種軍事和社會的意義。封建領主在僕人們的簇擁下,用暴力和經濟兩種手段使其債鄰屈服。 另一個主要的結果是小農的消滅,儘管這種結局的出現時悲慘的,然而卻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一結果對和平民主的發展過程做出了重大貢獻,其意義不亞於過會力量的加強。它意味着現代化能在英國順利地進行,而不受巨大的反動保守勢力——這種勢力存在於德國、日本的某些領域(如果不提印度的話)——的干擾。當然,這也意味着英國歷史進程中不會發生中國和俄國式的革命。 在英國,商業和工業界的精英們受到貴族習慣的一定影響。1914年以前,(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這以後的一段時間)英國的所有情況都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即延展的綠色田園和鄉間別墅對政治家和社會名流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自18世紀70年代以來,土地財產越來越成為一種地位的象徵,而不是政治權力的基礎。
書評
20世紀最令西方人費解和着迷的問題,來源於劇烈的變動和事實,一些國家鞏固和發展了民主,而一些國家卻走上了專制之路,進行了驚人或者駭人的國家實踐。在此之前,中國、日本、印度等非西方文明往往不進入歷史學家的研究視野,因為,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在19世紀60年代的歷史講稿中所表明的,歐洲學者關心的主題是那些顯然關乎現在並且關乎未來的過去,而其他的文明在當時還未明顯同西方文明相匯。 然而,在現在看來,事情遠非如此,殖民和世界大戰使這些彼此陌生的世界激烈碰撞,結出相互關聯的社會政治果實,這些聯繫遠遠早於布克哈特手稿完成的1868年,至少在巴林頓•摩爾看來是如此,從現代化最引人注目的標識法國大革命開始,一直到當代,在歐洲、北美及亞洲發生的重大變遷,猶如一條關節粗大錯落的巨蛇,一次擺動由頭部漸漸蜿蜒傳導至尾部。 這一意義深遠的擺動,便是現代化,摩爾在《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一書中,以這樣的視角進入東西方社會歷史,這些歷史於是錯落跌宕,在不一致的起點和不同的道路上總體上前後相繼,這種基本的觀念形成他分析的起點。 作為同樣的一個從社會角度進入不同國家的比較研究著作,摩爾與其他一些重要的學者在方法上的一個重要不同是,他在各國紛繁複雜的社會現實中努力尋找眾多差異中的共同之處。馬克思•韋伯也對歐洲、印度及中國社會進行過卓越的比較研究,但他的做法是,例如研究中國,主要關注中國社會中與西歐類似但又有區別的條件,以此揭示中國社會結構最恆久的方面和特徵。 摩爾在對中國社會的分析中,也考察種種制度與社會結構的細節,如宗族制、官僚文化、土地制度等等,但他的目的在於揭示走上不同現代化道路的不同社會的一些一致性因素,他有着更為穩定和明確的宏觀框架——在現代化道路中,至關重要的幾個因素——土地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力量均勢、土地貴族的衰弱、商品經濟的發展、反動階級聯盟的形成以及是否發生革命粉碎過去,大部分的社會細節均指向這幾條線索,在那些走向有效民主的國家中這幾個條件逐一具備,而另外一些國家,則由於缺少了這些條件中的一個或者幾個而與民主失之交臂。那些社會文化的細枝末節,有一些促成了條件的形成,有一些則導致了偏移。 上述五個條件的比較框架,表明了摩爾最基本的分析工具與馬克思主義分析工具相同,經濟基礎與階級分析,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階級鬥爭亦明確的給予批評,將各種非經濟的因素納入考察中,同時認為同一階級也並非鐵板一塊,有着各種各樣的分化,不同階級在不同階段聯合和對抗對歷史的走向產生重大的影響。對摩爾所持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對抗思維進行籠統的批評是不中肯的,特別是在仔細閱讀之後,便可以發現他與採用其他視角的理論進行了深思熟慮的對話。 與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評一樣,詳述這樣的社會史也極耗筆墨,然而它清晰的邏輯結構卻可以使我們確定一些感興趣的問題展開探索。在摩爾的研究中,對於中國農民社會和農民革命的論述占據了不少的篇幅,但其論述和線索散落在各個章節中,有時僅僅是隻言片語點到為止,與其他一些中國農民的研究相對照,也許能更好的了解這一主題。 摩爾考察的主要國家裡,有一些國家發生了劇烈的農民革命,而有些卻沒有,人們便要探索什麼樣的社會結構或者歷史環境會促成或者阻止革命。中國便是發生了浩大農民革命的國家,人們早已認識到中國革命產生的農村基礎的決定性作用。摩爾認為,兩個因素導向了農民革命,首先是在農村中缺少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商品經濟革命,第二是在給農民加上新的壓迫枷鎖時,切斷了農民與上層社會的聯繫。這兩個因素看似簡潔,卻包含了經濟、政治結構、社會文化的種種信息。 在開始探索中華帝國的特徵時,摩爾澄清了一種普通的認識上的錯誤,將封建主義、貴族等概念不加辨明的加在古代中國上,馬克思主義將中國說成是東方專制主義的而非封建主義,中國社會的另外一項基本特徵--官僚主義也不容輕視。與歐洲不同,早在世界的現代化進程開始之前,中國政治已經解決了土地貴族們騷亂的難題,科舉制起到了吸納官僚聯合官僚與貴族抗爭的作用。在中國社會中,上層階級的權力和威望不僅建立在對土地財產的控制上,他們權力和威望本身就是他們壟斷官僚政權的結果,這兩種混合塑造了中國社會經濟形態以及上層階級與農民的聯繫的方式。官僚制與宗族制度結合,消除了地主發展商品經濟的動力,使土地的集中和財富累積變得困難。實物地租的形式同時不利於商品化。農業社會中生產配置也極大的影響了商品化的進程,中國往往用平均分配稀有資源的方式維持下層的支持,而不是通過勞動分工與合作經營擴大利益,因而保留了大量小農,同時激發了激進傾向。 在上層階層與勞動階層聯繫方面,中國的士大夫生活在鄉間,但並不參與實際的生產,勞動監督及管理,中央政權依賴官僚系統徵收稅款,不可能與下面建立緊密的聯繫,社會通過農村鬆散的宗族制度實行治理,作為儒生的地主以宗教和文化服務的提供獲得大體相稱的特權。在現代化進程開始並逐漸發展之際,農村原有的權力結構發生變化,農民原來用以聯繫的組織遭到破壞,大量無地的農民游離於社會之外,最終走向了革命。 摩爾已經洞察了農民起義的保守性,以及農民階級中各種各樣的分化,在摩爾看來,農民革命的結果取決於它同其他階級的聯盟,也是在這裡,他注意到階級分析的有限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摩爾強調了統治階級的行為對於農民暴力的方式和結果的重要影響,殘酷的鎮壓可能使農民起義停留在低級形態或者一蹶不振,在帝國統治的年代裡,中國統治者並未不斷遇到來自同等地位的其他統治者的軍事競爭,因此常備軍並未花費太多社會資源,同時也沒有十分強硬的鎮壓力。這種統治階層與農民反抗的互動對革命等集體行動的影響後來在蒂利和曼恩等人的著作中被更為詳細的論述。 在摩爾那裡,對於中國的宏觀論述將這一遙遠的國度視為一個統一的社會體,事實上中國社會在遼闊的地域上存在着很多差異。裴宜理在其《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一書中,也致力於討論農民暴力革命發生的原因。她看到的是,在中國內部,有一些地區農民起義頻發,而一些地區卻並不然,同時,在農民起義多發的淮北地區,階級分化並未明顯顯露,大多數農民都擁有自己的一小塊土地進行耕種,佃農的數量極其有限。而農民起義和暴力的發生,常常是超越階級界限的,因而農民革命不僅僅根源於階級差別,裴宜理在對淮北農民起義的研究中,提出地方環境對於農村社會的影響,與摩爾的理論相呼應的是,淮北高度變動的社會和具有風險的生產環境,造成了落後的農業和文化境況,一方面消除了商品經濟興起的可能性,一方面,造成中央權力與農村的疏離,使政權對於叛亂和革命的鎮壓力不足。與摩爾遠遠的觀察不同,裴宜理髮展了一種生態學分析的新視角,發現了北方與南方農民反抗的不同,在淮北,農民反叛和集體暴力出於謀生和獲取稀缺資源在策略上的最佳選擇,是掠奪式或者防衛式的,而在南方豐饒的水稻種植區,農民暴力的目的是抗捐和抗稅。而中國農民叛亂和集體暴力的行動,為中國共產黨發動農民革命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摩爾對於中國農村社會的論述,還忽略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便是國家權力在農村中的滲透。不過對這一因素的重視,大概是在國家研究範式興起之後才開始的,摩爾對於這方面的分析,集中於戰亂的資本主義的壓力下中央和地主對農民的壓榨加劇的總體的論述,後來對於這一問題探討的發展,開始從民族國家建構的新視角切入。一個著名的概念來自著名的海外中國研究者杜贊奇——國家權力的「內卷化」,它指的是在現代化的壓力下,國家政權開始向農村滲透,現代化的國家政權財政需求過快,與傳統的農業經濟發展不適應,削弱了原來鄉村中保護型的經紀體制,最後利用贏利性的經紀體制來徵收賦稅,從而導致的國家權力的內卷化。內卷化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使的農民境況加速惡化,地方權力陷入土豪劣紳之手。而研究內卷化現象的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與內卷化有着近乎直接的聯繫。「內卷化」這一概念,來源於對中國社會結構中「權力文化網絡」的認識,「文化網絡」並不僅僅是以文化為起點分析社會變遷的概念,而是指一套蘊涵政治權威的由組織和象徵符號構成的框架。最典型的是農村社會中的宗教和宗族組織。「文化網絡」代表了不能被國家政權強加凌駕的大眾信仰和地方權威。文化網絡將個體農民整合進鬆散的組織中,以集體的形式應對外來的變故。 國家權力在20世紀的擴大極大的侵蝕了地方權威的基礎,替換以一種掠奪壓榨式的腐朽權力。摩爾在描述農村社會組織的破壞時提到,中國具有嚴格財產要求的宗族制,將大批無地農民拋在了社會共同體外部,使他們與上層完全脫節,反映的大概便是這種內卷化的結果之一。 不論是生態學視角還是文化網絡的視角,都從更為細節和具體的方面豐富了對於農民革命發生的社會結構和歷史環境的因素的探討,既對摩爾的研究提出了挑戰,也顯示了摩爾觀點值得借鑑之處。對於中國革命與農民社會的具體關聯,我們今天仍然知之甚少,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與農村社會結構的深層關係,這些研究都僅僅提出了重新探索的起點。摩爾的著作至少可以表明,經濟基礎和階級分析法,如果能夠謙遜和謹慎的使用,仍然對於現實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和洞察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