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变之亟
| 论世变之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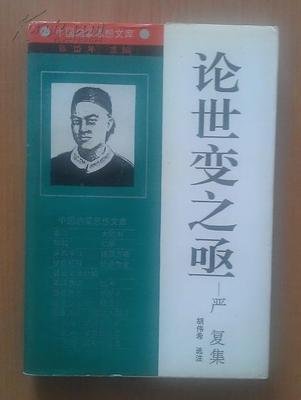 |
《论世变之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严复所作的文章,发表于1895年。该年2月至5月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了4篇文章,《论世变之亟》是其中的1篇。本文大旨在于阐述近代中国变化之快、之多,有尊民贬军,尊今叛古等内涵。
目录
基本信息
作品名称; 论世变之亟
创作年代; 1895年
作品出处;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
文学体裁; 议论性散文
作者; 严复
作品正文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构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浸多,镌镵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沉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抬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纮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曝腮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 嗟乎! 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盖自高颡深目之伦,杂处此结衽编发之中,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浅人怙私,常詈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忠爱之道,固如是乎? 周孔之教,又如是乎? 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 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 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 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自胜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马嘉尼之请不行,东印度之师继至。道咸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此郭侍郎《罪言》所谓:"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自蒙观之,夫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祸之发也愈烈。不见夫激水乎? 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不见夫火药乎? 其塞之也不严,则其震也不迅。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乎? 且其祸不止此。究吾党之所为,盖不至于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虑所万不及知,而闻斯之言,未有不指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夫为中国之人民,谓其有自灭同种之为,所论毋乃太过? 虽然,待鄙言之。方西人之初来也,持不义害人之物,而与我构难,此不独有识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为大诟者也。且中国蒙累朝列圣之庥,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谓横目冒耏之伦,莫我贵也。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叩关求通。所请不得,遂而突我海疆,虏我官宰,甚而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舆。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谓有人焉,伈伈伣伣,低首下心,讲其事而咨其术,此非病狂无耻之民,不为是也。是故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污,求驱夷之策者,智虽囿于不知,术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何以言之? 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 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观之,仆之前言,过乎否耶? 噫! 今日倭祸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 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 尚忍深言也哉! 《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又曰:"瞻乌靡止。"心摇意郁,聊复云云,知我罪我,听之阅报诸公。
白话译文
看如今的世事变况,大概自秦代以来没有像这样迅速的了。这世事的变况啊,人们不知道它的缘由,强行将其定义为时势。时势已然形成,即使是圣人也无能为力,大概是因为原本圣人也是时势中的一部分。既然是其中的一部分,说他能谋取时势并改变它,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些圣人,不过是知道时势的趋向,而预见它的去处。只因知道时势的趋向,所以才能承继遵循它变化的规律;只因预见时势的去处,所以才能重视时势而不与它违背。然后对时势加以调节掌控,使天下归于安定。后世的人因而看到圣人成就的功业,就像圣人确实能改变时势,而不知道圣人实际上从最初开始就未能改变它。就像是如今中日两国的结仇交战,探究它的缘由,这岂会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呢?
曾指出中西方之间的处理事物的方式,其中最不同而完全无法相合的一点,莫过于中国人尚古而忽视当下时势,而西方人则力求以当下超越古时。中国人把太平盛世与乱世相隔,国家兴盛衰败交替当作是上天主宰的自然的循环,而西方人把每天无穷尽地进步,国家兴盛后不会再衰败,社会太平昌盛后不会再动乱,作为学术研究、政治教化的最高准则。大概我们中国圣人的心意,是说:"我不是不知道宇宙是无尽的宝藏,人心的灵慧如果每一天都能开导它,在机巧之术和智能方面就可以逐渐达到无法测量估计(的地步)。但我却将其放在一边,不把它当作一回事,那是因为百姓的生存在于相安相养罢了。"天地之间的物产有限,但是百姓的贪欲是无穷尽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对物产的发掘每一天都在扩大,这终究会走向物资不足的趋势。物产不足则必定会起纷争,而纷争则是社会稳定的一大祸患。所以宁可将知止知足作为教育感化(的内容),使人民安居于鄙俗愚昧之中。劳动人民尊长敬上,所以便有了"春秋大一统"的主张。春秋大一统,就是全面平定纷争的局面。大秦销毁兵器焚毁书籍,它的作用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吧。顺延而下到了宋朝以来的科举考试,它防止纷争就更为深远了。拿人人都尊崇信奉的典籍,让人反复深入研读他们,而典籍的道理又常常介乎于似远似近,似有用又似没用之间。制定标准来招揽这些读书人,使得最聪明的人也有不一定能成功之忧,最愚昧的人也有偶尔成功之庆。然后对全天下中智慧杰出的人和稍有想法的人,张开八股文的大网捕捉他们。即便间或遗漏几只能吞没船的大鱼(指有能力的人才),他们已经遭受挫折,颓然老去了,还怎么去做推波助澜等事呢?可悲啊!这还真是圣人禁锢天下人,平定纷争消除祸乱的最高明的方式啊,然而人民的智谋就因此日渐低劣,人民的力量也因此而日渐衰弱。到头来,继而发展到了不能与外国人争夺一天生命的地步,这是圣人所没能考虑到的啊。即使这样,到现在这种局面,我们仍然闭门造车,如果跨海的轮船无法到来,能遁地的飞车没有途径过来,那么中国的百姓,与异族便老死不相往来了。富贵的人一直享受他们的财富,贫困的人一直安于他们的贫穷。通晓福泽青天的道义,就能做到秩序分明;推崇柔和谦让的教化,就能止息纷争。偏远的灾难虽然频繁,有弥补的方法;盗贼虽然多,有围剿灭绝的办法。这样虽然说不上是大治之世,但起码百姓也可以相互生活安定了。而谁能想到祸患常出现在考虑之外,继而西方人忽然出现,进入了我们的社会之中,于是我四千年历史典章制度,便有了涣散不能终日的担忧了。到了今日才开始知道它的弊病,和齐桓公感受到疼痛之时才接受治疗有什么不同呢!
和中国人谈论西方的治理,常常苦于难以说明它的本质。存在对中西方彼此成见的人,不明察事实,就说中国是讲究礼法道义的地方,而东南西北,凡是我王朝的威灵不能到达的地方,都是边远异族。这是第一大蔽塞。明理有见识的人,想要全国人民都客观清楚地看到中西方彼此的实情,他的评议是不能不体现出是非好坏的公道评判。然而肤浅的人坚持私利,常常责骂(有识之士)美化仇家而背弃本宗,这又是一大蔽塞。却不知道只是满足于自欺欺人的小聪明之中,却使得常受他族的侵扰侮辱而无能为力。忠诚仁爱的道义,本来是这样子的吗?周公和孔子的教化,又是这样的吗?各位思考一下,如今的夷狄,不是古时候的夷狄了。如今人们看待这些(被称作夷狄的)西方人,以为他们只是善于计算,又擅长技巧之术罢了。而不知我现在所见闻的,比如制造蒸汽机和兵器这一类东西,都不过是西方文明的支末,就是所谓的最精通于天文历算和自然科学,这只是他们擅长的事的端倪,而不是其中(西方兴盛的)关键所在。那关键是什么呢?我抓重点说,不外乎就是在学术研究上崇尚科学,在刑法和政令上公大于私罢了。这两者,和中国最初的理政之道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之所以他们运用起来常常成功,而我们常常失败,那只是因为自由而不自由的区别罢了。
自由,实在是被中国历代圣贤所深深畏惧,并且从未被确立为教育内容的东西。那些西方人的理论说:上天生下了人,使他们各自拥有天赋予的权利,得到自由的人才是完整的。所以人人各自得到他们的自由,各个国家各自得到它们的自由,只管致力于不让它们互相侵略损害罢了。侵犯别人自由,这是违逆自然法则,且违背人伦道德的。那些杀人伤人偷窃他人(的行为),都是侵犯人的自由到了极致(的表现)。所以侵犯人的自由,即使是一国之君也不可以,而那些法律禁令章程条例,大体上都是为了这件事而设立的。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西方的自由(观念)最相似的地方,是宽恕和法度(并用)。然而说他们相似可以,说他们确实相同,就大大不可了。为什么呢?中国的宽恕与法度(并用),是专门针对待人接物来说的。而西方人的自由,则既指待人接物的方式,但实际指的是一种人的本质。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便造就了中西方相当多地方的差别。我大致地举出一两件(异处)来讨论:就比如中国人最看重三纲五常,而西方人则首先强调平等;中国人亲近亲人,而西方人崇尚贤者;中国人依靠孝道来治理天下,而西方人以公正治理天下;中国人尊崇君主,而西方人则尊崇民权;中国人看重政令一致,风俗趋同,西方人则喜欢结成群体来聚居,各为其政;中国人大多避忌隐讳,而西方人多讽刺批评。对于钱财的使用来说,中国人重视减少支出,而西方人重视增加收入;中国人追求敦重朴实,而西方人追求现世的欢愉。对接物待人来说,中国人赞美谦恭含蓄,而西方人则主张直接;中国人崇尚繁复的礼仪,而西方人(在这方面)则较为简易。在致学方面,中国人夸耀博学之士,西方人尊崇创新的人。对于灾难祸患,中国人将其托付给上天命数来解决,西方人则依靠人的力量解决。像这一类的例子,所列举的有和中国道德伦理相违背的,在这二者之间,我实在不敢仓促地分出它们的优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