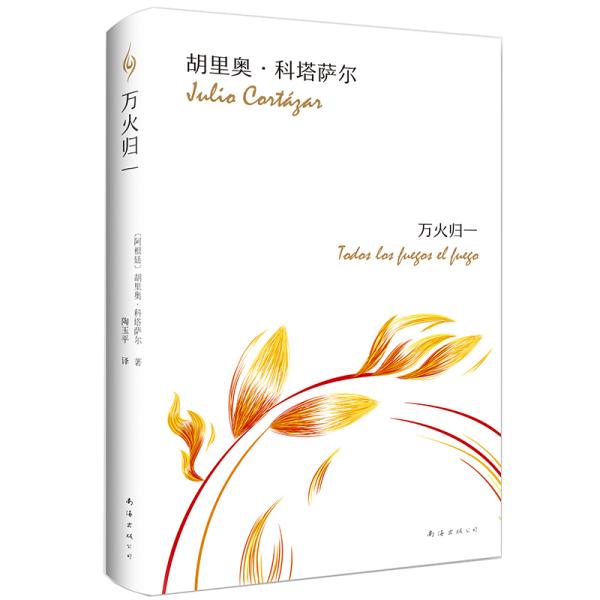万火归一
内容简介
在有限逼仄的空间内,将自身的意识和想象发挥到极限。午夜的公路上、飞机的机舱内、冰冷的病房中、玻璃穹顶的天空之下……科塔萨尔的笔下诞生出一个个奇特扭曲、坚韧隐忍的灵魂,他们挣扎着逃脱既定的命运,即便火焰已不可抵挡地团团包围 。
本书是胡里奥·科塔萨尔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收录有《南方高速》《病人的健康》《会合》《科拉小姐》《正午的海岛》《给约翰·霍维尔的指令》《万火归一》《另一片天空》八部短篇。小说构思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展开,一如作家往常的风格,随着情节发展逐渐剥离出失控和荒诞的一面,将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思议的复杂情绪以超然的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简介
胡里奥·科塔萨尔阿根廷著名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代表人物。1914年生于比利时,在阿根廷长大,1951年移居法国巴黎。著有长篇小说《跳房子》,短篇小说集《游戏的终结》《万火归一》《八面体》《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等。1984年在巴黎病逝。
科塔萨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实验精神的伟大作家。《西语美洲文学史》的作者奥维耶多说:“每当想到科塔萨尔的名字,人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迷人。”
原文摘录
他能做的只有投身于车流,机械地随着周围的车辆调整速度,头脑一片空白。 车流以时速八十公里的速度朝着渐行渐增的灯火驶去,却没有人真正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匆忙,为什么要在夜间公路上置身于陌生的车辆之中,彼此间一无所知,所有人都直直地目视前方,唯有前方。 “你们大家对我太好了,”妈妈说话时带着柔情,“你们费了那么多心思,一直不让我难过。” 罗克舅舅坐在她身旁,快快乐乐地抚摸着她的手,说她在犯傻。佩帕和罗莎假装在橱柜里找什么东西,她们明白玛利亚·劳拉说得对;她们明白了大家在某种程度上一直都知道的事实。 “一直照顾我……”妈妈说道,佩帕紧紧抓住罗莎的手,因为这句话让一切都恢复了原状,这漫长而必要的喜剧全盘复原。可卡洛斯站在床前,看着妈妈,仿佛知道她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现在你们可以好好休息了,”妈妈说,“我们不会让你们再这么辛苦了。” 罗克舅舅想辩白两句,可卡洛斯走到他身边,用力捏了一下他的肩膀。妈妈一点一点陷入了昏睡,最好别去打扰她。 葬礼后的第三天,阿莱杭德罗[小儿子]的最后一封信到了,信里一如既往地问起妈妈和柯莱丽雅姨妈的身体状况。是罗莎拿到的信,她把信拆开,不假思索地读了起来,泪水突然涌出,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抬起双眼,意识到自己在读信时,心里想的是怎么告诉阿莱杭德罗妈妈去世的消息。
书评
胡利奥·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正午的岛屿》的灵感不过是因为一次普普通通的飞机旅行。中午时间飞机正穿越爱琴海,他坐在舷窗前,看见一片深蓝色海中有一个奇妙的小岛浮在水面上。那一刻,他产生了一种神奇和非现实的感觉,因为那是一个无名之地,周围也没有人知道,然而他恰好就在它的上空,突然有种想到那里去的渴望。于是,他就成了小说中的乘务员玛利尼,每天经过这个无名之岛的上空,然后在作家的想象中,玛利尼代替他登上了那个岛屿。提到科塔萨尔的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他的短篇小说中迷人的特质:来源于经验和现实,但又具有强烈的非现实的幻想意味。
提到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经常会有人会拿他与博尔赫斯的短篇作比较。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博尔赫斯的短篇大都是来自于幻想的现象本身,是与现实无关的智力思辨的产物;而科塔萨尔的短篇虽然具有浓重的幻想色彩,但同时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就是说,幻想的东西产生于现实主义的情境,产生于每天的、日常的、普通人身上发生的再平常不过的事件。《南方高速》中一次高速公路上的堵车事件;《病人的健康》中儿女们为了避免母亲的丧子之痛撒下的善意谎言;《克拉小姐》中护士与孩子病人之间的微妙的感情纠葛;《给约翰·豪威尔的指令》中一个秋日的午后去剧院看戏的经历,等等。但科塔萨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从这种普通生活场景中抽离出一种非常态的、例外的、荒诞甚至神奇的小说特质。
接下来就是见证科塔萨尔小说中的奇迹时刻:回巴黎的高速公路上堵车了,科塔萨尔巧妙写下这个普通场景时特意避开了书写时间,仿佛时间静止了,前面的交通意外永远没有解决的可能,被隔绝在车里的人不得不在一个静止的时间里重新排列组合,像人类伊始踏入社会,他们选出领导者,搜集、交换和分配食物、水等资源。他们组合成小团队,成员有医生、看护、修女,处理突发事件者,应付外来入侵者,有条不紊地安排着被隔绝在高速公路上的“日常生活”,直到有一天公路莫名其妙的流通了。他们在高速公路上待了多久?为何堵车?又为何通行?我们都不知道,科塔萨尔也不知道。《南方高速》仿佛张爱玲笔下的《封锁》,时间打了一个盹,非常态时刻下的秩序井然又恢复了常态的混乱,各奔东西。年迈多病的母亲最疼爱的小儿子阿莱杭德罗突发车祸死亡,孝顺的子女为了对母亲隐瞒这个坏消息,他们特意制造了阿莱杭德罗远在巴西工作的假象,为了做得逼真,更要求那边的朋友以儿子的名义写信到家,一直到母亲去世。《病人的健康》中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写出小说中最后一个神奇的句子,妈妈去世后,儿女们收到了从巴西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信是罗莎接到的,她打开信,不假思索地读了起来,突然她抬起头,因为泪水已经模糊了她的眼睛,她意识到自己在读信的同时正在考虑该怎样告诉阿莱杭德罗母亲去世的消息。”
《给约翰·豪威尔的指令》更是荒诞味十足。瑞斯在一个秋日午后百无聊赖走进一家剧院,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被剧院的工作人员邀请到后台,随后就在胁迫下成了他刚刚还在观看的戏剧的男主角约翰·豪威尔。他刚刚入戏演到了第三幕又被莫名其妙地轰下了舞台,豪威尔换成了其他人,他又变成了另一个自己的观众。结尾的部分中,他和另一个豪威尔似乎遭到了追杀,逃离了剧院。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读者和书中的人物一样觉得莫名其妙。科塔萨尔给我们开了一个卡夫卡式的玩笑。对,这个迷人的短篇很容易让人想起卡夫卡的风格。把握真实世界曾经是小说定义的一部分,但是有没有一种办法即能把握住它,同时又沉湎于令人销魂的幻想游戏呢?即能严肃认真地分析世界,同时又不负责任地在梦幻的游乐中自由驰骋呢?“卡夫卡解决了这一难题,”米兰·昆德拉说,“卡夫卡在真实性的高墙上打开了缺口,许多别的作家紧跟着他各以各的方式通过了这一缺口。”这其中就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当然还有胡利奥·科塔萨尔,他们都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中的代表性人物。
关于拉丁美洲文学与欧洲文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地理上的距离使得拉丁美洲的作家远离区域性的环境,从而可以让他们意识到欧洲文学的大环境;但在这种欧洲文学环境的映照下又凸显拉丁美洲小说的独特的美学价值,即一种形式上的新颖性。如果说拉丁美洲作家群里有一个很好体现了他们与欧洲文学之间这种复杂难言微妙关系的作家,非科塔萨尔莫属。这一方面与他早年在法国的流亡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的多产以及对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极富探索的革命精神上。从《万火归一》这部短片小说集中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八篇小说中每一篇都颇具新颖,毫无重复累赘之感。尤其值得一提的《克拉小姐》这样的名篇,人物之间基本没有任何直接场景设置和对话情境,只有各自的心理活动,带动整个故事的发展。这种完全靠语言和句子本身的起承转合完成的小说不但实现了一种“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新型小说形式,而且体现了科塔萨尔在语言上的无比简约的风格和精湛技巧。借用米兰·昆德拉评价卡夫卡、穆齐尔、布洛赫等人的话说:“他们都是小说的诗人。也就是说:热爱小说的形式与新颖性;关注每一个词和每一个句子的力量;受到试图穿越‘现实主义’边界的想象力的诱惑;……完全专注于现实世界。”
胡利奥·科塔萨尔无疑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小说的诗人。